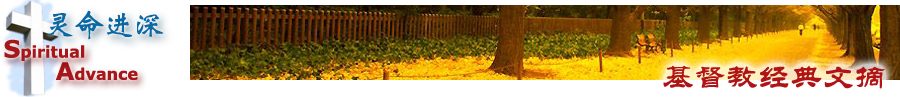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忻州日记
经文: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来二14)
「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不受预言结局的捆绑,因为在启示录五章,上帝透过祂敞开的门,在已预言过的结局上启示我们:『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祂是坐在宝座中的那一位,羔羊与狮子合併;祭坛与宝座合併。约翰在主后九十五年看到它,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相信它。
1974年4月,在泰国南部乡下痲疯病院,两位宣教士受到恐怖分子绑架,也走上羔羊的道路。」
(摘自:内地会宣教士麦亚瑟所着《为争战而生》)
简介
本文係根据Robert C. Forsyth编辑,伦敦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4年出版的《1900年中国殉道士》(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所记载的真人真事写成。文中传教士的活动和话语,绝大部分直接译自他们在逃亡过程中写的日记和信件。他们在被抓之前把这些宝贵的文字交给了忠信的村民们。最初,村民们把这些日记、书信埋在了地下;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了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由他们转交给殉道者的亲人们。
时间:1900年6月底至8月上旬
地点:山西省的忻州地区
背景:义和团在山西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
人物:英国浸信会忻州站的八位传教士
赫伯特.狄克松(邸松牧师)(Mr. Herbert Dixon)
44岁,曾在刚果传教,1885年来华。
狄克松太太(邸松师母)(Mrs. Dixon, nee Williams)
45岁,曾任伦敦儿童医院护理,1885年偕夫婿来华。
威廉斯.麦可拉奇(马牧师)(Mr. Williams McCurrach)
31岁,1896年来华。
克拉娜.麦可拉奇太太(马师母)(Mrs. Clara McCurrach)
31岁。
汤玛斯.安德伍(Mr. Thomas Underwood)
33岁,1896年来华。
安德伍太太(Mrs. T.J. Underwood)
30岁出头,幼为孤儿,1898年来华。
贝茜.雷诺小姐(任小姐)(Miss Bessie Renaut)
30岁,1899年来华。
西尼.恩纳尔先生(燕牧师)(Mr. Sydney Ennals)
29岁,1899年来华。
一、1900年6月29日,星期五
信使带着传道站给沿海地区的邮件到太原府去,但信无法寄走,就连夜匆匆赶回来了。早晨六点,他带来的消息令每一个人震惊: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 H. Edward)的医院给义和团烧了。医院的人纷纷逃出火海,女传教士爱蒂丝(顾姑娘)(Miss Edith A. Coombs)本来已经逃出来了,但她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有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里,要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的时候,额上遭了铁器的一击,扑通栽倒在浓烟里。她刚刚挣扎着爬了起来,又被人勐力推了一把,仰面倒进火里去了。第二天人们在残垣断壁中找到她烧焦的骸骨,就把她埋在院子的中央。其他的传教士先是逃进居所的院子里,但院门被冲开,他们便逃散了。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且把守了太原城门,防止他们逃走。
信使走了,空气凝重得像一块铅。早就不断有谣传说所有的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都要被杀尽。几个月前,怂恿义和团反教杀洋而遭罢黜的山东巡抚毓贤,到北京游说了一趟,得到「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垂爱,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四月下旬到太原上任来了。毓贤一上任,山西的义和团就活跃起来。六月初,保定府的义和团就切断了这里与沿海一带的联繫。四天前,传道站听见风声,就请县府保护,县府回话,不予保护(后来才知道,当时八国联军已攻陷大沽炮台,清政府已正式对列强宣战)。
现在,忻州传道站有三对夫妇和二位单身传教士,都是英国浸信会的:最年长的是狄克松夫妇,一对中年人,1887年来忻州医疗传道,开设了这个传道站。
麦可拉奇和安德伍年龄相彷,都是三十出头,1896年两人一同来到中国,又一同来到山西,就成了好友。英国浸信会在山西只有两个传道站,一个在太原,另一个在忻州。1897年的冬天,安德伍留在太原的传道站工作,麦可拉奇则到了忻州,来帮助孤军奋战的狄克松(那时,狄克松太太和四个孩子回英格兰去了)。麦可拉奇来后,狄克松就回英国去看望离别四年的妻子和孩子们。1899年,狄克松夫妇把孩子们留在英国上学,自己带着为医疗站所筹措的器材,返回了忻州,并且很快就开始为病人动手术。他们回来时,麦可拉奇和安德伍都不再是单身汉了──狄克松离开忻州后,安德伍的未婚妻怀特小姐到上海来,安德伍和她就在那儿举行了婚礼。同一时间,麦可拉奇也在上海与传教士克拉娜小姐成婚。有了贤内助,麦可拉奇和安德伍在这一带合力兴旺福音,狄克松不在时,教会仍然稳步发展,这实在让狄克松高兴极了。
这几天,安德伍夫妇刚好从太原府来看望麦可拉奇夫妇,躲过了太原的灾难。而传道站的新鲜血液,雷诺小姐才来九个月,恩纳尔先生也只比她早两个月,他们年龄只比麦可拉奇小一两岁。十几年的经营,这个传道站相当有果效,狄克松培训的一批中国传道人十分得力,年轻的帮手们也到了,新的房屋也快盖成,……正当狄克松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狄克松深邃的眼睛像他的手术刀一样敏捷而沉着。他首先打破了沉默,大家合计了一下,事不宜迟,应该赶紧离开这里到山区去,忻州不过在太原以北一百四十多里,义和团随时都可能出现。与他们在一处的中国传道人何全奎,传道站的厨子安叔根,还有贝茜的助手张陵旺,一个聪明的少年,也觉得到山里去避难好。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地从西门出了忻州城,没有遇到什麽麻烦。他们先是往太原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后来就岔往西南去。
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经过中国信徒张其国老汉的家门,就过去敲他的门。门开了,出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戴着苍色的瓜皮帽,个子不高,像柏树一样的结实,这就是张老汉,当地最早的信徒之一。这几天风声很紧,张老汉正在为传道站担忧,见到狄克松他们,喜出望外,一摆大手,就招呼大家进屋来,让牲口歇歇脚。过了几个时辰,大家吃完晚饭,就听见外面由远而近响起达达的马蹄声。狄克松正要起身,信使已经跨进门来,告诉他们说,忻州县的兵丁正在四处搜寻他们呢。天擦黑时,他们告别了张老汉,继续往前赶路。
急急地走了一个时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就等在那儿,有几个中国基督徒要领他们到藏身处去。
半夜的时候,他们牵了毛驴来了。大家顺着一个枯水河床前行,鹅卵石不时硌着脚跟。三位太太骑在马背上,丈夫牵着马。贝茜和西尼骑着毛驴。有时一脚踏进水里,溅起一片哗响;有时又踏着沙地而行,布鞋里灌进了沙子,不得不脱下鞋把沙倒出来。领路的弟兄走得较快,不久就把传教士的伫列抛在后面。没有灯笼,又不敢喊前面的人,大家就在一个岔口处走失了方向,绕了几里路回来,在一个狭路口遇见响导,他们正焦急地等在那里。
大家一同前行,爬上了一段崎岖的山路。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这个山村叫刘家山,就是他们要藏身的地方。
这是逃亡的第一天。
二、1900年6月30日,星期六
但他们不敢在白天进刘家山去。村里有不少基督徒,一般的村民也极友善,白天进去本来是无妨的。只是近处山上的寺庙在办佛事,有香客来往,传教士们怕给村子人带来麻烦,就退到峡谷里去,藏了一整天。
夏天的雨,像竹林一样緻密,在风中摇曳。他们浑身湿透,坐在石头上,脚下是浑浊的激流,雨一直喧闹到半夜才止住。夜里,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东西,颠簸了六里多的山路,进了刘家山。
三、1900年7月1日,主日
为避开拜佛的人们,传教士们必须先藏起来。天亮之前,男子们翻到山的另一边去,藏在一个山洞里。女士们则藏在地窖里,用盖子掩住洞口──这几乎要了她们的命。再晚一点拖出洞来,她们就不行了。后来乾脆呆在窑洞里。半夜,男人们才回到村里。
安叔根和张陵旺也到刘家山来了。大家为太原的传教士们担忧,又不知他们的近况,就请安叔根和张陵旺到太原去打听一些消息。
不知怎麽的,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他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麽而死,又是怎样死的,至少应该对他们有个清楚的交代。他平时就有在日记本上写几句的习惯,从逃亡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不间断地写下所经历的一切。也许是受他的影响吧,贝茜和西尼也开始各自记下自己的心迹,而威廉斯则给自己在英国的母亲写信。汤玛斯很安静,花了很多时间来默祷。
四、1900年7月2日,星期一
传教士们藏在信徒兰万牛的家中。他家坐落在小山谷的起头,两边都是峭壁,堂屋是从山坡上掏出来的,是极安全的地方。传教士们在祷告中常常记念那些纯朴的中国信徒们,不知他们的境况如何。他们被称为「二毛子」,也就是「汉奸」,是不配活着的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更大。狄克松是瞭解这些北方农夫的,他们眷恋自己的故土,即使房子烧成了灰,也不肯走远,彷彿有一条绳索栓住了他们的心。他们也极重亲情,常常回去找失散的亲人,幸好青纱帐起来了,或许他们可以藏身。
下午来了一个中国信徒,说代州的信徒遭难了。代州是忻州以北一百八十多里的县城,义和团兴起来的时候,信徒陈志韬的一家分散开来逃离。年过半百的母亲,裹脚走不远,就近藏在一座庙里,很快就被义和团发现了。他们把她带到一座阔口嘻笑的大肚佛像前,要她下拜。老人是信独一真神的人,脖子挺直一声不吭。「看样子你一定个是二毛子了!」一个拳民上前来劝她,「何必认真呢,你磕一下头就成。」老人还是不应。「不磕头,上香也成。」有人递过来一支香,「甭管你是不是真心的。」 老人开口了,「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拜假神的!」「那是你自己找死了。」在围观者的哄笑中,她被杀了。血从她的颈项上涌出来,淌进尘土里,一个小小的血泡鼓起来,无声地破了,血浸入地底去。
庙外面响起纷乱的脚步声,陈志韬,还有他的父亲和兄弟也被抓来了。拳民先用烙铁烙伤了他们的脚板,这样他们跑不了。然后把他们三人用板车拖回代州去,要向义和团的首领报功。幸好县衙的门生听到所发生的事,就等在衙门外,看见板车过来,就和差役过去,把他们截下来,告诉义和团,「县衙门要审明这些人后再加以严办。」听说以这种方式,那个门生救了十多个人呢。(在那个以权为法的社会里,对信徒的迫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权贵的人格品质。有一个信佛的地方权贵,以为杀二毛子是积阴德,竟把所有捉住的基督徒,不论男女老少,都杀尽了。)
五、1900年7月3日,星期二
又有信徒来,报告崞县的情况。崞县在忻州和代州之间。29岁的张葵其实还只是慕道友,但在村子里已被认为是基督徒了。他逃进邻村时被抓,就地被砍死了。
威廉斯铺一张纸在膝盖上,给自己的母亲写信。「我们处在丧生的危险之中。」他顿了顿,接着写道,「现任巡抚恨外国人,要把我们都杀绝了。按他的命令,所有的官员拒绝给我们保护。我们原来打算从东北逃出去,但北方比我们这里乱得更早。保(定)府乱得厉害,我们绝对不能逃走了,……这是中国黑暗的时刻!但如果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杀了,这又将会何等地感动教会!如果这是神的方式,以此将福音传遍中国,我们就决然准备好,为福音的缘故而死。我们中没有人愿意死,但我们都诚心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他屈指算了一下,继续写道:「这是逃亡的第四天了。听说兵士们正在搜寻我们,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抓走。这几天总是下雨,也许神是以此来救我们。神不是曾从监狱里把彼得救出来吗?祂也可以如此救我们,如果这是祂的旨意。」他看了看周围,天光几乎被云严严地封住了,屋子里一片昏暗。「不多写了。雷诺小姐和恩纳尔先生的记事比较全。也许这是我给您的绝笔了。」
威廉斯看了看坐在身边的妻子克拉娜,俯身吻了一下克拉娜翘翘的鼻尖。他重新把信纸摊好,又加上几句:「我和克拉娜一直在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愿你们大家都能和我们在天堂相会。亲爱的妈妈,不要为我们难过。如果我们死了,我们会死在一起,同进天堂同得冠冕。」
传教士们决定在山里挖洞,夜里就开始行动了。
六、1900年7月4日,星期三
除了狄克松要照顾生病的太太外,三位男子这两天睡在草料屋里。今天,西尼看见三个义和团从山下的村子上来,停在他们躺卧之地的下面歇脚。其中两人抬的是食物,另一个抱的是衣服,不知是从哪个信徒家里抢走的。他们走了之后,西尼在日记上记下了这一险情。「几乎不可能尽述境况的悽惶,但我们大家都因信靠主而内心有奇妙的平安。」他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为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祂的名,……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祂赋予软弱者的能力,……。」
傍晚,安叔根和张陵旺从太原回来了。他们打听到,传教士和他们的子女们加上法尔定本人,都被囚禁在法尔定的住所里,毓贤已经判处了他们死刑,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拖出去杀掉。
威廉斯眼前浮现出洛维特医生(罗医生)(Dr. A. E. Lovitt)骑着枣红马出诊的样子:他穿的是皂色的对襟棉夹袄,捲起的袖口露出白衬里来,头上扣一顶瓜皮帽更显出前额的宽阔。洛维特的医术使他在太原远近闻名。他救人的命,如今却要为此丧命。洛维特太太呢,她一定抱着他们的婴孩杰克,哄他不要哭吧。还有别的人……。
大家迫切地祷告之后,威廉斯找出昨天写的信,加上了太原的情况。「他们还没有遇难,我们为他们的脱险祷告。上帝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作好了死的准备,如果这是祂的旨意。若有兵丁来抓我们,我们会逃到另一处去。因为主曾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太十23)愿上帝救助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也愿祂安慰你们的心,这是爱你们的儿子和女儿的祷告。」
四个男子──狄克松,威廉斯,汤玛斯和西尼,忙于挖洞,女士们则在家里为他们祷告。如何掩埋挖出来的新土,让他们费了一番心思。
七、1900年7月5日,星期四
安叔根和张陵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的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两人都被认为是该死的。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了,是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个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个人,稀奇他们竟然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有发话,就听见少年激烈地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于是他们被杀死,尸身又被扔进火里烧了。(他们遇难的消息并没有传回刘家山,传教士们一直到被抓之日仍在等候他们的音讯。)
八、1900年7月6日,星期五
刘家山还算平静,但不断有邻近传道点的坏消息传来:繁峙的传道点被烧了,两个基督徒被烧死,其中一个是传道人。代州的传道点也被烧了。崞县的和奇村的传道点均遭抢掠。
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默祷。真是对信心的严峻的考验啊,西尼像燕翼一样浓重的鬍子在抿紧的嘴唇上抖了抖。儘管来华传教的时间不长,还在学习语言阶段,但他从狄克松,麦可拉奇身上学到了信心的功课。他打开日记本写道:「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一二一1-2)祂真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信靠祂,在万事上信靠祂。求主快来解救祂的儿女们。我们也预备好了来迎接那属于我们的冠冕。愿主在我们中间作证。」
九、1900年7月7日,星期六
男人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挖洞,天亮前回村休息。大家每天还是读经祷告,在其中获得极大的安慰。西尼在日记里继续写道:「我们的时间在神的手中。主是我的光和拯救,我还怕谁呢?每时每刻信靠主。啊,主所赐的平安!我们要天天经历它,更多地经历它。如果主呼召,我们将快乐地回答:我在这里,请按你的心意而行!妈妈,明天是主日,愿主与妳,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讚美主的时候吧。」
十、1900年7月8日,主日
今天举行了露天敬拜。这是逃亡之后,大家一起度过的第二个主日。在这似乎是最没有指望的日子,大家开始数算主的恩典,喜乐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眸子。没有一个人后悔到中国来传福音。
狄克松太太还是很虚弱,她不得不把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狄克松最后讲起自己的身世,他平时忙于传道,很少完整地讲过自己。双亲去世的时候,狄克松才十一岁。他进了伦敦孤儿收容学校,在那里被主的灵得着了,有感动要将福音传给远方的异族之民。他的心在刚果河畔,并为此作准备。经过三年大学训练,他被浸信会刚果传教会接纳为传教士,然后接受了两年的医药和外科训练。在那里他结识了威廉斯小姐,并在去非洲之前两人订了婚。他在非洲忘我地工作,但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之后,他因四肢麻痺而不能行动,被送回了英国,在威廉斯小姐所在的医院治疗。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几个月后他竟奇蹟般地站起来了。但医生再也不准他回刚果去了,他就申请到中国来。他们在1884年年底结婚,转年春天夫妇俩就出发到中国来了。早先的几年他们在太原与其他传教士传福音,太原的传教站是1877年山西旱灾时建立的。那时,山西十室九空,几百万饿殍载地,野狼食人肉而肥。传教士进入山西赈灾,旅行佈道,并在太原等地建站。原来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传教是以戒烟为先导的。后来狄克松夫妇到忻州开闢传道站,狄克松太太的护理经验,还有她在妇女工作上的热心与献身精神,给狄克松不少帮助。狄克松在忻州忙得不亦乐乎,戒烟、医疗、每日讲道、到乡村传福音,渐渐显出果效来。
太阳落山了。望着金光弥漫的天空,西尼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心因主的恩典而充满了讚美之声。这些日子让我们得见救主的面。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位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我要说,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淨,我们就更加讚美祂,因祂看我们值得为祂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十一、1900年7月9日,星期一
这一天出奇的平静。得不到外界的一点消息,太原被囚的传教士们生死未卜。
傍晚出去挖洞之前,狄克松提议为太原的友人们特别祷告。大家紧紧地围成一圈,肩膀靠着肩膀,低着头跪祷。那些熟识的名字一一地被提起,从一张口传到另一张口:
法尔定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Rev. G. B. Farthing, Mrs. Farthing, Ruth, Guy and Baby)
斯丢瓦特小姐(Miss E. M. Stewart)
怀特豪斯夫妇(Rev. S. F. Whitehouse, Mrs. Whitehouse)
洛维特夫妇和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杰克(Dr. A. E. Lovitt, Mrs. Lovitt and Baby Jack)
斯都克夫妇(Mr. G. W. Stokes, Mrs. Stokes)
辛普生夫妇(Mr. J. Simpson, Mrs. Simpson)
贝农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女(Mr. W. F. Beynon, Mrs. Beynon, Daisy, Kenneth, and Norman)……
末了,狄克松太太用微弱的声音,提起爱蒂丝的名字,就是6月27日在太原被烧死的。
当他们轻声念着这些名字的时候,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了。
十二、1900年7月10日,星期二
去忻州打听消息的人还没有回来,大家为此而焦急。
今天威廉斯分享了自己的见证。16岁的时候,这个苏格兰少年重生得救了。他的生活明显地改变,参与当地教会的事奉,时时留心训练自己。当时,有来中国传道的传教士回英国办事,到他所在的教堂去演讲,中国就抓住了少年人的心。大学毕业后,威廉斯成为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1896年秋天时启程来中国。他说:「来中国传道,是我渴望已久的梦。当我踏上海轮的甲板时,那种兴奋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笑了一下,「不过,唯一让我有些伤心的,是要和母亲分别。」今年4月的时候,他和克拉娜一起到忻州北边八里远的一个村子去佈道,村民友善地待他们,并且不少人决志信主。他们回来后,赶紧给在英国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毫无疑问,这样的佈道中得帮助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信徒,我们自己的灵命也得到振奋。我们最感恩的是,慈爱的天父给我们这样的特许,向这广大的民众传福音。我们仰望祂,跟随祂,将祂自己的道传讲出来,带着祂最丰富的恩膏。」
克拉娜在一旁作些补充。她也稍微提起自己的事。她从小就想成为传教士,一个女孩子想到异国他乡去传道,令他的父母不能理解。她成人之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她的父母也就转而支持她。她与威廉斯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了。
十三、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
刘家山的一个村民被抬回来,浑身是伤。这几天,他一直惦记着他那嫁到邻村的女儿,坐立不安,劝都劝不住,今天一早就到十五里外的村子去看他的女儿。刚到村口的井边,就被义和团撞见了。不由分说,就认定他是受了洋教士的指使,要在水井中投毒。要不是他女儿家的人赶来,他就被打死了。义和团放出风声,说星期五要到刘家山来。看样子,传教士藏在刘家山的事,也许走露了风声。
晚上十一点,去忻州的人回来了。忻州的官吏因为任传教士们逃走而受到了上头的责罚。传道站的房子已经遭窃。有一百个义和团从忻州出来了,毁坏着附近天主教的村子,也在寻索狄克松他们。
洞已经挖成了,虽然不大,但是够传教士们藏身的。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里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这样,刘家山的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己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连累了刘家山的村民。
传教们马上分头出去,让村民分散,儘早离开村子。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这些天一直与传教士们在一起。他也离开了刘家山,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何全奎老汉今年60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是传教站忠心的同工。
看着何老汉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后,传教士们才回到村里来。他们捲起简单的行李,带上些乾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夜半的时候转移到新挖的洞里去了。
十四、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
洞挖在一条河的坡岸上,离刘家山有一段路,刚好够大家躺下。河水在洞口下面3里远的地方流着。昨夜他们已经在河里提了两桶水,放在洞里。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都被杀了,是在星期一被杀的。他们从法尔定的房子出来,被领到衙门附近的房子里,山西巡抚毓贤也到场了,他们一一被杀。没有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有一声争辩,只有几个幼童看见他们的父母倒在血泊中时吓得哭起来了,但没有一个孩子倖免于难。太原的传教士中,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只有她在被杀之前,为那些平静受死的传教士,包括自己被杀的丈夫,也为自己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有人害你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麽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有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他们被杀之后,又有天主教的12个人被杀。同天被杀的还有内地会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地押解来的一些传教士。连6月27日被烧死的爱蒂丝在内在太原府殉道的共有46人。
传教士们明白,一旦被捉住,是决然没有活命的指望的。
十五、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
夏夜,一片静谧;山下疏落的村子里,早已熄了灯火。大家出洞来,在野地里睡觉。汤玛斯枕着一块石头,看见一颗颗宝石,高高地嵌在天穹上,垂下清澈的光芒来。安德伍太太躺在近旁。自从确知太原的朋友们殉道的消息,他们俩都无法说清心里的感受,既为他们生命的见证骄傲,又因过去的友情搀杂了一些伤痛,甚至心中泛起一丝疑惑,神为什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他的忠僕们身上。现在看见拱垂的星光,汤玛斯忽然想起雅各在伯特利所梦见的天梯来。他喃喃地说出了雅各当时的惊诧之语:「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创二十八16)他又一次坚定了自己的心,造天地和人类万物的神掌管一切,在殉道者的血流过的地方,必定有更丰硕的收穫。
在一个博大的怀抱中,大家安睡了一夜。
但白天,狄克松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不得不完全呆在洞里,也不许说话。村民逃走了,没有人送食物。必须节省食物。」他左手撑住瘦削的下颚,闭上双目默祷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抬起谢顶的头,望瞭望狭小的洞口,就着透进来的光继续写道:「我们的洞至少有一个外人知道了。但神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祂。我们的性命是祂的。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甚至肯捨弃自己的性命来保护我们。」写到这里,狄克松的眼睛湿润了。这样的人民啊!为主的道受难是值得的,为拯救失丧者的灵魂而受难是值得的。
贝茜给浸信会写了一封短笺,附在她的日记上。她写道:「从日记中你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境况,……神在帮助我们。祂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来作艰难的攀登。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的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中都是忠信的。」
何全奎老汉离开刘家山之后,东躲西藏地潜行,好不容易接近了忻州城。他的妹妹一家就在城边的一个村子里,他就进村去看看她,打算在她家歇歇脚。想不到村子里几个18、19岁的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一见面就把他抓了,押到城里去。
忻州县衙现在是新上任的徐贵丰。徐贵丰以为找到了传教士们藏身处的线索,急忙升堂,要查个水落石出。何老汉上着手铐,拒绝说出一个字来。徐贵丰冷笑一声,把他交给衙役去杖笞。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地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是没有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仍戴着手铐,扔进了监牢。与他在同一个牢房的,正好是个基督徒,就千方百计地照料他,但人已经给打废了,只能喝得进几口水。(4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十六、1900年7月14日,星期六
外面是酷暑天的毒日头,洞内阴湿而且闷热。燕麦饼也快告罄了,这是这几天传教士们的主食。狄克松提议开一个特别的祷告会,向天父求食物和带领。
在狭小的洞内,一个人的左手拉着另一个人的右手,形成了一个圈。大家跪下来,开口轻声祷告。
祷告刚刚完,就来了3个人。两个是刘家山的村民,另一个是外村人。他们带来了些粗麵作成的大饼。「真好啊,是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祷告的人们会心地笑了。村民们说,刘家山已经空无一人了。山下面五里开外的傅家庄的人,便到村里来行窃。
一个村民捏了捏洞中的卧具,已经湿透了。狄克松解释道,「这个洞非常阴湿,卧具上潮了,但我们不能晒,一晒就会被人发现,附近的几个小山上都可以看见的。」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带你们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去,那里有一个老洞,乾燥一些,也大一些。」
大家说好明天晚上搬到那儿去。
十七、1900年7月15日,主日
炎热。骄阳似火。传教士们藏在洞中。又有两个村民来了,送来几个粗麵的饺子。大家感动得不知说什麽好,因为村民们自己也很艰难,自己也没有吃的。
今天是主日,狄克松领大家在洞里静默祷告,是一次特别的家庭聚会。
夜里,大家捲起铺盖,外面下起了暴雨。等到一点半钟,昨天的那几位村民还是没有来,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什麽拦阻。大家只好打开铺盖,重新在洞里躺下。
十八、1900年7月16日,星期一
整个上午豪雨如注。群山烟雨朦胧。一直到下午二点,还是没人来。
今天早晨,狄克松太太几乎昏迷过去。躲藏已经18天了,狄克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能坚持多久呢?只剩下几块饼乾,沙丁鱼,和一些奶。看见女士们消瘦的脸就难过。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麽。刘家山的村民不敢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人看见,或走了,或藏了。每个村里都有义和团训练,就人来看,我们到了绝望的极点,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
夜里,几位村民来了,送给传教士们一些食物,还有一个人带了些水来。他们告诉传教士们,二佑子和他的兄弟及夏奎子这几个人,打算出卖传教士们了。他们拦阻人来送食物,要把传教士们饿死。
十九、1900年7月17日,星期二
下午,又有村民来,说太原府来的义和团到处在找忻州的传教士们。狄克松平静地说:「我们仍在神的手中。」
接着,村民又讲起了赵喜茂一家的事。赵喜茂是忻州的一个信徒,他的母亲和姐姐也都信主,他刚过门的媳妇也信主。村里的人都劝他快逃,但他就是不肯走,结果义和团一来就把他们一家四口抓起来,绑了,用车送往忻州去见义和团的首领。首领懒得见他们,说:「在哪里抓的,就在哪里杀了!」回来的时候,这四人在车上一路唱着圣诗《主引领我前行》。到了村外空地,拳民把赵喜茂拖下车来,用铡刀铡断了头。然后对3个女人说:「你们只要说自己不信,就可以活命!」赵喜茂的母亲(57岁的老人)说:「你杀了我的儿子,也杀了我吧!」结果被杀害了。剩下的两个人手拉着手,还是很坚定,作姐姐的说:「我的母亲和兄弟都死了,你也杀了我吧!」最后只有赵喜茂的媳妇站在那里了,她才19岁,毫不含煳地说:「你杀了我的男人,婆婆和姑姐,我还有什麽活头?你也杀了我吧!」就这样一家四口都殉道了。
狄克松和麦可拉奇都记得赵喜茂,一个像泥土一样质朴的人。他是远近闻名的基督徒,在村民中素有好名声。历史将证明,中国基督徒在苦难面前的见证,至少和罗马大迫害时期基督徒的见证一样高贵!
晚上,听见山下腾西沟村人声喧嚷了一阵,最后平静了。
二十、1900年7月18日,星期三
早晨六点多,一个村民来告诉传教士们,昨夜30-40个义和团从腾西沟村往傅家庄去了。在傅家庄,约有100人聚集。
他一大早就上山,急忙赶来报信。大家并不认识这个村民。「这个洞有很多人来过了,恐怕不安全。另外有一个洞,离这里约莫有三里远的路,你们不如现在就跟我到那边去。」他气喘嘘嘘地说。
传教士们祷告求神的引导。西尼祷告道:「慈爱的父神,你的天使在我们前面行。只有你能拯救我们!如果是你要我们以死来荣耀你的名,想见我们戴着殉道者的冠冕与我们的主同在,就充满喜乐。我们将面对面与主耶稣相见,并且与祂同行。主必会带我们进入天家!」
大家心里有平安,决定只带一些必须的卧具,马上转移。天已经大亮了,传教士们紧跟在村民的后面,贴着山坡,急速地往前走。在白天一队人行动,是非常惹人眼目的,幸好时间不长,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所说的山洞。
这个山洞比较大,而且也不阴湿,只是尘土重一些。在新的洞里安置下来后,狄克松又开始记日记,他觉得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近了,就更加急切地记下所经历的一切。末了,他写道:「神知道一切。我们信靠神,祂会拯救我们。但我们也愿意死,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
到现在为止,大家所写的日记和信放在一起已经有一叠了,成了一本小小的书。谁能帮我们把它转交给我们在英国的亲人呢?──大家并没有太多的疑虑。凭十几年与中国农民相处的经验,狄克松深知这些善良的村民们。他们遵守着「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古训,十几年前得到的帮助,还一直记在心里,自己的生活已经十分艰辛了,还是克扣自己甚至自己的孩子,省下食物来,冒险送给我们。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可以託付的,可以请他们把这些东西交给后来的传教士。想到这里,狄克松道:「愿神赏赐那把这本书,转交给朋友之手的人。」
晚上,狄克松和西尼回到原先的洞里去,在路上并见两个村民,就和他们一起把没有带走的卧具,还有一些埋在地下的食物,一起搬到新洞来了。
二十一、1900年7月19日,星期四
昨天下午,大家发现这个洞还连着另一个小洞,通过一个狭小的通道就可以进去。小洞的顶,已经崩塌得厉害。于是,威廉斯和西尼爬进去,做了清理的工作。大家就在那个洞中之洞里过夜。虽然挤一些,却是好的藏身处。但如果被出卖了,则无处可逃,也可能被烟呛死。
昨夜来了四个人,从两个村子来的,带了一些杂粮做的食物,要换银子。他们说所有的都被清军封锁了,有义和团从太原来,不准人送食物上来。村民们走后,狄克松怀着感恩的心写道:「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当地的资源已经告罄,但神每天都给我们一些食物。」
这是逃亡的第21天。大家盼望着早日得到解救。但是出去的几个人,安叔根和张陵旺16天前往东边去,何全奎9天前往东边去,至今没有音讯!然而,狄克松是安静的,就像一个镇静的统帅一样鼓舞着大家。每一个人都像在暴风雨中安睡的鸟儿一样,拥有不能夺去的平安。
贝茜到中国来的时间不长,但她为此却准备了很久。在向浸信会申请成为传教士之前,她就刻意训练自己,在家乡的教会教主日学,每一节课都认真准备。后来,又接受传教士的训练。她的意志力就像坚石一样,而且很能帮助人。来到中国后,她就随狄克松太太一起,走村串户,向妇女们传讲福音和永生的道理,她的真诚让人实实在在地看见了她所信的。她今年30岁,传教生涯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她抿着嘴,嘴角上现出几分刚毅,低头在日记本上写道:「我们不是常说,我们宁愿与主行在黑暗中,也不愿独自行在光亮处吗?现在就是向主证明我们的诚意的时候。祂使我们有这样的诚意。」然后,她想起将来读到这些日记的英国的亲友们,也许会为她而伤心,就加了一句:「愿神给你们每一个人恩典来说,祂的旨意是最好的!我在祷告中记念你们。我爱你们!」
中午,不知为什麽事,山下几个村子里的义和团相互打斗起来。后来,就有人来把他们解散了。
二十二、1900年7月20日,星期五
平静的一天。只是狄克松太太病得厉害。夜里,来了一个人,带了些燕麦麵条,在洞口叫道:「麵条换银子,银子!」他是一个吸鸦片的人。塌陷的脸颊黄里透黑,两眼幽幽地看着人。
晚上11点,那个吸鸦片的人又来了,带了些煮熟的粟米来。他说,他见到30-40个义和团在他的村子里,不过5-6里远。在另一个村子里,也有太原来的3个义和团在训练村民,全都竭力要找寻藏在山里的传教士们。他建议传教士们搬到以前的洞里去。
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传教士们并不想打仗,只能逃。他们又一次包好了行李,搬回原先挖的洞里,是在分水岭的另一边。夜半的时候搬到那里去。儘管路不远,狄克松太太有3-4次因虚脱而跌倒,终于不省人事。狄克松揹着她,到了那个阴湿而又狭小的洞里。
二十三、1900年7月21日,星期六
早晨7点,狄克松在日记上记下昨夜的经历。「断了与外界的联繫,唯一可得的一些消息是来自一个吸鸦片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逃走了。我们信神天天在引导我们。如果不是有对神的信靠,我们早就绝望了。」
狄克松看着昏睡在洞里的妻子,想起她拖着病弱的身子,在崎岖的山坡上慢慢地挪动、最后昏倒的情形,内心忽然涌起一股对山西巡抚毓贤的愤恨来。这麽多天来,睡在潮湿的地铺上,躲在阴湿的或佈满尘埃的洞里,又没有一定的饮食,女士们的脸都是憔悴不堪!但他没有让这种苦毒抓住,写道:「但我们不能自己做什麽,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哦,主啊,愿你的救助早一点来!我们的孩子和朋友们,我们的爱。」
早晨9点,听见有声音在山头上叫:「牧师!牧师!」然后就沉默了,声音有点熟,但一时不能确定是谁。
几个男子赶紧到洞口去,看到有几个义和团装束的人站在山头上,显然在看着他们藏身的洞口。「我们被发现了!」洞里没有一个人惊惶。这些日子的试炼,已经把大家预备好了。
西尼和汤玛斯留在洞口观察,狄克松和威廉斯回洞里,赶紧检查那两把手枪,准备自卫。但那几个义和团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向洞口逼近。估计他们是在监视,要等人来齐了再下手。
下午快3点的时候,忽然有几块大石头从洞口上方滚下来,明显是要堵死洞口。狄克松和威廉斯马上冲出洞口,看见有50-60个义和团站在洞口上方,小石块如冰雹般地向他们打来。一个戴黄帽的青年,叫嚷着督促众人,自己也非常起劲地扔石头。狄克松就举枪瞄准了他。枪声一响,小黄帽应声倒地,滚到洞口下面的山谷里去了。其他的人一窝蜂似的跑到山头上去,然后翻过山坡,到山下的村子里去了。
大家到义和团刚才聚集的山嵴上去,看见一个人倒在血泊中。赶紧过去一看,原来是张其国老汉(他们逃亡的第一天曾在他家歇脚)。他脖子上的伤口是义和团所致,也是他们惯用的杀法,就是从侧面割破血管,让他慢慢地失血而死。血流了一地,那顶苍色的瓜皮帽浸在血泊中。他显然已经死了几个时辰了。手被反绑着,牵他的绳子被扔在一旁。显然他们在什麽地方捉住了他,要牵着他看这场袭击。但是他在山头上大声叫喊起来,要给传教士们发出警报。刚才就是张老汉的声音!他救了传教士们,使他们有所戒备。
威廉斯和汤玛斯,还有贝茜下到山谷去看小黄帽。他还活着,只是伤了头皮,伤得并不重,不久就会恢复的。但是没有东西给他包扎。他看样子是个领头的,20多岁的模样。威廉斯和汤玛斯从山谷底提了水来,贝茜就给他洗伤口,他大声地呻吟着。大家也不再呆在洞里了。
傍晚贝茜打开日记本写道:「我们坐在山谷里,在这麽多天的洞穴生活之后,觉得外面的世界是多麽美好!但这种美好又似乎是一种嘲弄─我们身边是那个受伤的年轻人的呻吟,滚在谷底四处的那些大块的石头。我们只有举目仰望神,向祂祷告。」
晚上9点,见大家对他很友善,小黄帽开始跟大家说起话来。他说,这批义和团是从新州南郊来的,是杨老爷乡里的人,杨老爷与新任县长是亲戚,县长就派他们来抓传教士们。
「你们什麽时候抓住张其国老汉的呢?」狄克松问道。
「好些天前,他上路要来看你们,在路上被贾庄的人抓住了。张老汉的村子多半是信耶稣的,贾庄的人跟他们是对头,因为他们不捐钱修庙。后来我们忻州的义和团到了贾庄,就要他给我们带路,他死也不肯。后来我们还是从别处知道了你们的洞口,就把他拖来了。」他们杀张老汉不为别的,只为他是基督徒。贝茜听到这里,感动得流下泪来,喃喃地说:「他在荣耀之中了。再过一两天,我们就会面对面地感谢他了。」
狄克松详细记下这一切,并且写道:「我们到了人的尽头。愿主引导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杀死他们任何一个人,只是把他们赶开了。我们也许不能活着写更多了。我们在神的手里,希望有得救的可能。」然后他又照例写下这样一句:「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监护人。」
他们所记的日记在此中止了。晚上有一个村民冒险来看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包好了交给他。
尾 声
过去的几天还算平静,但他们显然已被监视了,无处可逃。
7月25日,忻州来的一队清军到达这里,领头的对传教士们喊话,放枪要抓住他们。大家看抵抗是无益的,就跟着清军出来,被押送到忻州去。到了忻州,见过新任县长,就被投入公牢,在那里有两週之久。详情并不为外界知晓,只知道那个牢狱素有「虎口」之称,狱卒的贪欲,囚室的秽浊,又时值酷暑,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方。
8月9日,太原来了个官长,带着10个兵丁,传山西巡抚毓贤的话,说要把传教士们护送到海边去。传教士们从监狱里出来,看见四辆旅行用的车等在外面,就信以为真,欢欢喜喜地上到车里去。车行至城的内门处,早有一群义和团等在那里了,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传教士们被拖下车来,像囚犯一样被扒光了上衣,推到城外砍头,尸体被抛在小河岸上。从附近的村子王家庄出来一群粗野的人,以最羞辱的方式虐待了传教士们的尸体。其实,他们与传教士并没有什麽血海深仇,只不过是人性中的恶,在得到了许可甚至以为是义举的情形下,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了,远远超过了平时遮遮掩掩所行的,因而也远非兽性所能概括的了。
但周城有一个绅士为此伤痛。他雇了几个人,收拾了传教士们的遗体,把他们掩埋了,就埋在城外的牆脚之下。事后,还时常有忻州的人,向儿孙追念起这些传教士们所行的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