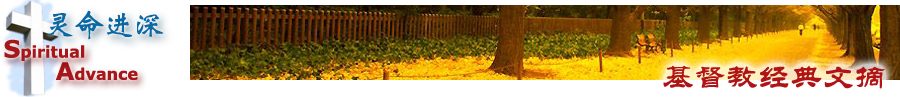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补篇 福音使徒孙大信
孙大信持守著主给他的亮光,传福音,到了西藏,因此也就牺牲了他的生命。我们盼望从这种牺牲捨命的成功上,在西藏能多多的结些果子。孙大信自从归主以来,他的目的是要引导西藏归从基督。从前他曾经到过那闭关自守的西藏一二次,照本书而说,他在西藏已经受过二次危险,幸而能安然的脱离了。
在这本书《孙大信略传》出版的几年之前,他又辞别亲友,不惮跋涉山川险阻,去到他所最爱的西藏。这一次自从他投入了那高山峻岭之后,即从此逝去,自此再没有人见过他的踪迹。但现已经得著正式的报告,知道他确实死了。如此,在基督的运动上,就失去了他的踪影;只是在历史上,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他有灵性上的特别经历;虽然他不是一个前进的人,但他的见证确实能够感动人。
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位非凡的门徒,完全将自己奉献于主。无论如何,一提到基督的圣名,他就满面出现喜乐的光辉。虽然他以作基督人为乐,然而他的面上留有作基督人的苦难伤痕。他是一位最大的奥秘派,也是一位谦卑的人。他和保罗能同样的说见过了基督,但他决不因此自夸。他是最谦卑的人;虽能叫听众恭敬他,但不愿人宣传他声望。人们都很佩服他、敬爱他,看他是一位圣人。
他作主的门徒,毫不畏死;他以为基督死而荣耀基督的名为乐的。他现在已经与世长辞了,他的奉献,常留在我们的心坎里。基督教会失去了一座柱石,一座能力的塔,确是教会的一个损失。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临死的地点、如何死法,不过神的僕人摩西也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死是得胜的。他脱去了肉身的限制,而享受天国无限的喜乐。
“我听见天上有势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著他们。”(启十四13)
关于他死后的消息,有1933年5月11日的《英国週报》(The British Weekly)刊载出来,现在节录如下:
“四年以来,终日悬在我们心目中的孙大信的生死问题,现在已经正式证实,他已经死了。我们朋友虽然都存著一分很淡而微的盼望,指望他仍旧在喜玛拉雅山的深谷中活著,但经印度政府各方面的消息,证明他确实死了;我们只能承认这是一个确实的消息。从此,基督的圣徒为主而殉道的,又增加了一人,因为他完全是为西藏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
“我(记者)与孙大信最后一次的见面,是在1925年;他在我动身到戈卡(Kotgarh)之前,他特别跑到新玛(Simla)来看我。我的印象觉得他那时正是直接的从撒巴杜(Sabathu)痲疯院中出来。
“他满面带著沉重的病容,十年之前的那种虎虎生气,现已消没殆尽。面部上涌现著痛苦,声音也低弱到几乎不能听见。他到了这个地步,然而仍急切的盼望到西藏去。我们又谈到北印度信仰的进步;注意,他每一提到他的主人耶稣基督的名,他面上立刻容光焕发,眼中发出奇异的光彩,好像幻见了基督实地站在他面前一般。
“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两种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他的面容,他的面容上面含著无限的痛苦和忧愁,是我从前没有看见过的。我想他这种痛苦和忧愁,也许是因为许多愚人疑心到他的真诚和纯洁问题。这是从旁的一方面听来的;如果属实,那就无怪他感觉灵敏的天性,要觉得这种痛苦,比他身上已经受过的各种痛苦还要难受。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刚才我说过的;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向下低垂著,只是每一提到了他的主耶稣基督,立刻他的头也扬了起来,面容上发出了光辉,尤其是他的眼中,射出了奇异美丽的光彩。
“史脱克(Samuel Stokes)告诉我,有一次,他同孙大信到山中去,他们所要经过的是喜玛拉雅山中最险、最劣的一条僻径,他们翻越了许多险阻。后来到了这最险、最劣的僻径口上,他们的力量是已经用竭了,气候十分寒冷,并且大风暴也来了,他们掺扶著走了几步,就仆倒了。若是没有行人经过,他们必死无疑,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知觉。幸而恰巧有几位行人从那里经过,他们将二人从严寒的山道上抬到一间茅屋中,救活了他们的生命。
“史脱克又说了一件关于孙大信的事,也是在喜玛拉雅山的深山中;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必须经过一条小溪;但是在大雨之后,山水爆发,这条小溪,成了一条急湍的河道。他们若要过去,必须等到水落之后;可是孙大信竟走入水中,被急流卷得沉下去了。对岸有几个山中居民,立刻跃入水中,将孙大信捞救了起来。在这几乎丧命知觉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孙大信告诉史脱克说,他沉到水底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见有天使用手扶持他,将他送到了岸上。我听见了史脱克的话,就推想到孙大信在半失知觉的时候,他的主观的内在生觉能力。对岸的人跳入河中去救他,变成了他半失知觉时候异象中的天使。孙大信的异象,和史脱克在岸上亲眼所见那些山中居民入水救人的主观现象,谁能说不是一样的实在呢?
“关于我最爱的朋友的纯洁生活,现在我要略说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他的品行,本是放射著灵性的光辉,其中却有一件更华美的成分,即是那一种逃避声望的方法,因为他觉得这种声望是他在灵性上的重负。
他旅行到西方去的时候,基督教界完全向他开放。教会的大领袖们都邀请他讲道,欢迎他到他们的家中,如同招待圣人一般。在印度本国,他的美誉是随著他的脚迹而走。只是这种声望使他觉得如同重负一般,极力的逃避,也就成了他属灵伟大的见证。最后,我们见过面的一次,他也提起过这事,并且说明这种声望确是一种重负。他对这种声誉毫无兴趣,他的心是完全注意在一个更高的目标上;他始终是决意为基督的缘故,要到他所深爱的西藏去。西藏人虽是一再的想要将他置之死地,然而他仍旧奋勇的前去,要想赢转他们的爱。
将来这些事虽记在书上,传布到了西藏,我们几乎不能疑惑将来这些山中居民和中亚细亚的人,也许能了解有一个人背著主耶稣的十字架,准备将爱献给他们,尤其属灵伟大的,就是愿意为他们捨去生命。”
“对于这一位为西藏殉道的孙大信,真可以说,‘一个人为他的朋友们牺牲生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以上是安得斯(C. F. Andrews)之报告。
又《英国週报》5月18日之通讯如下:
“读上期贵报(指《英国週报》)安得斯论到孙大信的一段文字,我十分感激,尤其是感谢他为孙大信证明一切事实。他是一位圣贤,有的人竟冤诬他是江湖之流,这是由于西方人不了解东方人的缘故,确实是一件可怜的事。
“1920年,我从旧金山乘船到澳洲去,凑巧碰见与孙大信同船,这是我一生引为最荣幸的事。这一次的航行确实是可记念的,尤其使我永远不能忘却的,乃是这位东方的基督奥秘派的伟大人格。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人如此的叫我联想到基督。无论怎样,在他的里面确实有些地方表显基督,叫人无法拒绝──就是外面上也是如此。在他的言语行为上,那种谦卑的灵,叫人不得不想到──不是想到孙大信,乃是想到孙大信全身、全心事奉的主人。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他,我所得的印象是出于意想以外的。正碰见我这时候染著小病,是坐的头等舱位。他却不然;这种异常的人格,在这船上发射出来,叫人感觉著有些惭愧的意味;因为他的人格中含著灵性上的分量,在那下等船舱外面安详的步踱著,叫人觉得同著那些平常习于头等舱位的人杂在一处,十分不安。这种印象至今仍是涌现著在我头脑中。这一次,在船上有许多机会使我能与这一位属灵人见面交通,叫我永远的回忆感谢。他为爱西藏人,冒险去传道,确实配戴上殉道者的荣冠。”
以上是英国伍舍司特会艾司福(W. J. Ashford)的通讯。同时,在该报另有一封来函,译之如下:
“我第一次看见孙大信,听他讲道,是在1920年;地点是在伦敦圣佐治会堂内。全堂拥挤不堪,人声轰轰不已。一会儿,孙大信静悄悄地走上了讲台,穿著简单宽敞的黄衣(凡修道的撒督都穿黄衣),头上裹著白色(或是米色)的布巾,手上拿著一本小《圣经》。他静悄悄的走进来,无声无譁,极其谦卑。顷刻之间就发现了一种物质上的奇迹;众人拥挤不安的现象立刻安定了,轰轰的声音也平静了,各种不舒服的情形也消没了,就是一根针落到地上的声音,也听得见。众人的眼光都注视著他。他并没有开口;我们却好像已经被移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好像到了天界。我常常注意,名人当著很大的群众,仅有物质方面的表现,决没有这样的功效。如此肃穆的平静,好像神圣的掌握捉住我们一样。你看见了他,就只知道他是一位充满了基督的人;基督也充满了他。他简直是属于另一世界的;他到这个世界来仅仅是一位暂时旅行的基督人。
“我第二次再看见他的时候,是在卫斯敏(Westminster)礼拜堂中;他和佐卫特(Dr. J. H. Jowett)同在讲坛上。这一天虽是天气很湿冷,但到会的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孙大信仍旧穿著黄衣,与前次一样;他的言辞简赅、冷静,并无修饰,亦无表情姿势;只是心中含有深沉、无欲望的热情。说话的时候,他有基督一样智慧柔和的光;我们的心都觉得如在神手中一般。如若全地的教会都能记念这位神的圣者,必定发达;因为他叫千千万万的人更加认识主耶稣。我想各地教会都应当记念他。”
以上是康丁登爵夫人朋纳基(P. Bonarjee)的通讯。
我们在5月25日又得著潘亚萨夫人一段通讯,潘夫人即是本书的原著者,兹将其原文摘译如下:
“从1918年以来,我与孙大信已成为很熟悉的朋友,1929年,他就到西藏去了。他允许了我为他作传记,他亲自供给了我许多材料。我们在印度的时候,他常在我们家中作客。1922年,他第二次到欧洲,又到过我们在英国的家。1925年,我们离开印度,他照旧与我们信札往来,表示十分的感情。他刚动身到西藏的时候,他又寄信告诉我们,谁知道这就是他最后的笔迹。
对于马哈利喜(Maharisha)的事,我很清楚。孙大信强健的时候常退居静处,专作默想和祷告的工夫,以达到成圣完全的地步。他两次到欧洲虽然不改他简单的常态,但是,一方面虽说对于天性的实验上得著经历,而对于健康的意念;在他的信中,常常有希望早脱离世界的思念,希望可以早些与神相见。有了这种心思,所以他决意再到西藏去会见他的一小部份信徒。他感觉到‘我应当作那差遣我来者的工。’他的心十分想念西藏的基督人,所以牺牲的意念愈加恳切。
1929年4月18日的信上写著说:‘我今天起程到西藏去,我知道这行程上的危险和艰难,但我应当顺从主的旨意。(徒二十20-24)如若神叫我仍旧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立刻就写信给你,否则,我们就等到神的脚前再会了。’
“孙大信所说的这些话,和在以前的信中所说的,他必定在六月之前,回转印度的话,没有什么比这些话还要动人。他素来说话极其信实,也非常忠诚,若是我相信他如有失信的可能,我也决不至于写出这些话来了。
“最后,自从他没有回来,又经过了细密的搜寻之后,证明他不能照著他向朋友们宣布的预定、计划办到,想必是他还没有走到有火车的地方之前,就遭了不幸,并且很快的灭了各种痕迹。”
另外在6月1日该週报上,又有一段通讯如下:
“读了几次所发表关于孙大信的文字,我也想起潘亚萨夫人书中的几件奇事。有一次,孙大信在尼泊尔一个小村庄中传道,引起了本地人的反对,村中的人就将他的手脚缚起来,绑在一棵树上。他又飢又渴,树上的果子也无法摘取,于是就晕去了。这样力竭气尽的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醒来,不知如何,手脚都鬆了绑,并且有一堆果子在他身边。
另有一次,他在丛林中迷失了道路,天色晚了,他走到一条河边。他正恳切祷告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我来帮助你’,同时,就看见一个人从对岸投入水中。这人游水过来,负起孙大信又游到对岸。孙大信看见地上有火,便就著火烘自己的湿衣,那知一回头,那人早已不见了。
这二件事和许多其他同类的事,都可说是一种不认识的朋友们暗中相助;也可说是人类中神的天使。只是像下面这段事,那就更为神奇了。
孙大信有一次经过西藏一片荒僻的地方,村中的人对他极其仇视,因此他无法入村,便在一个山洞中藏身。不多一会儿,便看见许多村人拿著木杖和石头渐渐逼过来。孙大信觉得命终的时候到了,便祷告将灵魂交给神。村人逼近只差几步,忽然停住,并且又后退了几步,彼此遇遇交谈。一会儿,他们又上前问孙大信:‘那一位身穿白衣站在你身边,还有许多白衣人围绕著你的是谁?’……那些村人于是求孙大信到他们家中去。他向村人传福音,他们都信服了。
孙大信表显出主耶稣的爱,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事,决不以为希奇,必定很简单的说:‘我知道神伸出祂的手拯救了我。’这些事迹正是告诉我们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许多神迹关于‘不可思议的原因’,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是不可以轻易丢弃的。潘亚萨夫人说,凡是与孙大信接触的人,‘没有不被他那平静的心和他圣哲的言语所感动。’”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著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十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