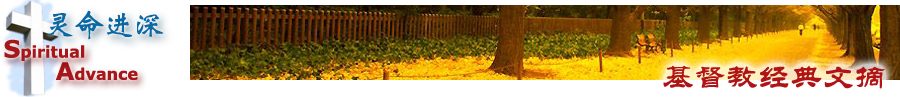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威伯福斯——克拉朋联盟创始者
张文亮
没有人知道这个制度起源于多古老的历史;
没有人能算出有几千万人像条狗似的,
毫无尊严的死在这个制度下;
没有人能理解那些号称古老文明、智慧结晶的
罗马、雅典、中国、印度、埃及、波斯……
不仅挡不住这个罪恶制度的蔓延,
而且默默的欢然享受这个罪恶带来的甜美滋味。
所以奴隶制度,几乎被画为
胜利与权力的象征;
经济祭坛上必须焚烧的廉价祭物;
社会阶级合理存在的不合理制度。
单单在非洲,至少有
一千五百万人被掳到伊斯兰、
一千万人被卖到欧美大陆,去当奴隶。
谁能来为奴隶的痛苦申诉呢?
一七九○年,在英格兰的克拉朋,
有八个年轻的基督徒,不同的专长──
历史、文学、财经、法律、教育、企管、外交、政治,
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
却有相同的信仰与异象,
一起奋斗三十六年。
以立法的程序、不费一兵、一卒,没有流下一滴鲜血,
挣断了罪恶的奴隶制度,
解救千千万万的黑奴。
这一群弟兄就是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
一、没有机会跌倒的孩子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生于1759年8月24日英格兰东北部的赫尔(Hull)港。赫尔港不像伦敦码头那样的吵杂;也不像利物浦(Liverpool)港满了黑奴贩子的咒骂,除了几只啼叫的海鸥和着货物搬运工人出力的吆喝之外,赫尔港安静的像赫尔河的流水,默默地滑入大海。河畔的山丘上有一幢红砖造的大厦,威伯福斯十二岁以前经常由窗口远眺,看港口大街上奔跑嬉戏的孩子,他看得好羡慕,但是他不能出去。远溯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英国逐渐强盛的海上贸易,威伯福斯家族赚进了许多的财富。可惜人丁不旺,到了1750年代,整个家族只剩下威廉.威伯福斯(以下简称威伯福斯)这一个男孩子。于是他很小就饱受妈妈与一堆婶婶、阿姨严密的呵护,还有许多仆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威伯福斯既幸福又可怜。他经常发脾气,希望也能像一般的小孩子在户外奔跑,就是跌倒了也无妨,不希望在过多的关怀里,连跌倒的机会也没有。
二、忧郁的腌瓜
1771年威伯福斯终于有机会离开赫尔城的红粉堡垒,在妈妈、众姨婶、婢女们的千叮咛、万交代中前往普克林顿(Pocklington)中学就读。普克林顿在当时已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是英国最昂贵的学校。学校林木茂盛,片片金色的阳光洒进古老修院高耸的尖塔,几位来自一流大学的教授,带着少数的学生,穿梭在藏书丰富的知识殿堂中。以昂贵学费筑起的学习空间,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是这几乎扼杀了每个学生的学习胃口,过度地美化学生与老师的亲近,结果老师们把好的教出去,却把人格上不好的东西也在无意间倒了出去。例如圣琼斯(St. Jones)大学来的教授巴斯喀特(Baskett),丰富的学问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生命的喜悦,只有自视过高、怀才不遇的苦闷,其教学的结果,如威伯福斯在家信中写道:“他是很好的人,教书也颇认真;但是老师经常忧郁,一上起课来,教室里的同学,就像浸渍在忧郁瓶中的腌瓜,个个沉闷的打不起精神来。”在这里书读不好也被合理化了,更增加学生懒惰的藉口,能念多少就算多少,反正到这里来的学生,即使一辈子不赚一分钱,也有用不完的家产在等着他们。
三、文学与打牌
威伯福斯不爱上课,不过,中学六年他学到的两样东西,影响了他的未来。一是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尤其擅长背诵古诗,让自己沉闷的忧郁随着抑扬起伏的朗诵音调,流泻在大气中,这培养出日后他成为议院雄辩者不可或缺的文雅气质。二是打牌,威伯福斯过目不忘的认牌本领,及冷静分析对方出牌后之企图的能力,使他屡打屡赢,给他带来日后的自信。
1776年10月他进入剑桥大学文学系。他不喜欢数学,很早就自认是数学绝缘体。本来以为剑桥的自由学风,对文学的喜爱有更多的催化。但是太容易的课堂内容,没给学生带来什么挑战,他索性白天在上课时睡觉,晚上到城外游荡、喝酒,直到深夜才爬回寝室挑灯打牌到天亮。不久获称为“英格兰第一牌客”,为了打牌什么事都可以停摆。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良习性,日后反而使他很快的打入议会政治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在牌局中,让他觉得虚空,觉得每个大人物,包括自己,都有一张见不得人的底牌,而使他认真地寻求,如何做才能使自己人生的底牌变王牌。
四、政治生涯的开始
1779年他认识一个与他不同典型的朋友皮特(William Pitt),皮特的父亲曾担任英国首相。皮特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准备将来从政。皮特课余就到伦敦议院听议员对法案的辩论。有一次他邀请看来无所事事的威伯福斯与他同去。
正反双方激辩的言词,像是一把猛锤,敲醒了这个混沌剑桥赌客的心田,一下子把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与政治辩论的巧妙措辞结合在一起。之后二年,两人不断往返伦敦与剑桥。毕业后相约在议会场上见。1780年的春天,威伯福斯在赫尔选区,以剑桥文凭,家族企业的势力,与带着古典文学优美词句的辩论,最高票当选议员。
初进议院,许多政治企图强烈的新议员,就像乍回河川的蛙鱼,力争上游。威伯福斯没有什么野心,也缺乏有力人士的引荐,开始只是静坐一旁,听人发言。一天,一些资深议员在会后相聚打牌,看威伯福斯既年轻又富有,就请他加入牌局,心想这家伙一定是很嫩的肥鸽子,很容易骗得他身上的每一块钱。威伯福斯微笑入座,以出神入化的技术掌握输赢,像个拉手风琴的人,把他们的钱袋,像音箱似地时而放大,让他们赢钱;又时而压小,使他们输钱;末了让每个人的本金又回到自己的钱包,为这场游戏画上句点,而且除他以外,每个人都觉得又惊险、又可惜、又愉快。就凭这与政治无关的技术,威伯福斯成为政治圈里的新宠。在1784年的法案辩论上他崭露头角,他清楚的思路、嘹亮的声音、感人的词句,在人看来,俨然是政治界的明日之星。
但是威伯福斯却不快乐。愈接近政治权力的核心,愈看清个个似乎都在为国家福祉执行公务的人,私底下却是追逐权力与巩固自我。政治像是牌局,只有输赢,没有同情,而自己又逐渐的深陷其中。虽然有群众称赞他的辩论是如何折服人心,通过法案,赢得选票;可是这一切又好像是美丽的泡沫,一下子就破灭了。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烦恼使他天生的视弱症更加恶化,有时几乎看不见东西,必须依赖别人读给他听,医生劝他要多休息,才能缓和病情,但是政治上的成功使他无法停下。
五、做导游的事奉
1784年10月,威伯福斯带着母亲与妹妹赛莉(Sally),前往地中海的里维埃拉(Riviera)游览。当时的英国贵族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邀请一位大学老师作陪,到欧洲游历,这称为旅游教育(grand tour)。在剑桥大学,米纳尔(Isaac Milner)教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生导游,不仅风度翩翩,而且见多识广。威伯福斯见过他后,在日记上写道:“他的谈话非常生动活泼,”就邀他参加。米纳尔不仅是个受人爱戴的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很容易相处、平易、踏实的人。陪学生去长途导游旅行,是他工作以外的另一个事奉。把福音传给威伯福斯的就是他。
六、跨出信仰的第一步
旅行团在10月20日经过多弗(Dover)海峡到法国的加来(Calais),再顺着隆河(Rhone)下里昂(Lyons)、尼斯(Nice),一路上景色宜人。威伯福斯与米纳尔相处愉快,一路上谈笑风生。一天威伯福斯批评一个名叫史蒂令弗立特(James Stillingfleet)的牧师说:“他真是一个极端的人,”米纳尔问道:“为什么他是极端的人?”“他竟然宣称上帝就是那个犹太人耶稣,而且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哦!那怎么算是极端呢?”威伯福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开明的剑桥教授,竟会反驳他的看法,在他的印象中,基督徒是一群愚昧、不用大脑、墨守教条的狂热分子。威伯福斯理直气壮地答道:“根据索齐尼派(Socinian)的看法,这宇宙有神,但神是不可知的,圣经怎能阐明呢?而且神是全然真善美,怎么会是耶稣呢?”米纳尔在隆河边的沙滩上停住脚步,定睛看着威伯福斯。他的眼神消失了平日的诙谐,露出了威伯福斯从未见过的认真说:“如果你只是要争辩,那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要严肃的讨论,寻找真正的答案,我愿以最大的喜悦回应你最凶猛的炮火。”威伯福斯突然想起在驿马车的行李箱中,有一本没看过的老书,是道得理治(Philip Doddridge)着的《信仰在心灵中的跃升与长进》(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他奔回马车,把书给米纳尔看,米纳尔说:“这是相当精采的一本书,让我们一起读、一起讨论吧!”
认真的慕道友至终成为认真的基督徒。一路上两人不断的在旅途中讨论书中的内容,并且仔细的查考圣经。1785年2月回到英国,威伯福斯几乎查考完圣经里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也清楚地认识上帝、耶稣基督与人的关系。他深深地渴慕要认识真理,六月再邀米纳尔到瑞典一游。两人沿途仔细查考希腊文圣经,不断地讨论。风景区是游玩的地方,对威伯福斯来说,那是他专心注目、更多阅读圣经,与米纳尔讨论的地方。威伯福斯以前认为基督耶稣的信仰,不过是一套道德的规范,一种看事物的逻辑,没有耶稣的信仰是一种脱离束缚的聪明。到了9月,他才认清没有耶稣的信仰,在根本上是一种堕落人性主控的堕落信仰。威伯福斯到了老年,回忆这次旅行的收获:“信仰的真理对我变得很清晰,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即使现在有人告诉我,死后会沉沦下地狱,我仍要在地狱中喜乐。”
七、心灵的黑夜
从瑞典回来后,威伯福斯继续他的政治生涯,却突然发现信仰使他没办法再继续昔日的生活。他厌恶议院里的政客,他说:“议院像是挪亚的方舟,里面都是野兽,没有几个真正的人。”并认为过去自豪的辩论,是“无形的虚空”,整个生活、工作与信仰成为连不起来的线。他每天一早起来祷告,但是帮助好像不大,愈敬虔反而落入更深的失望与烦恼的深渊,信耶稣的喜乐彷佛云消雾散。他写道:“我非常的难过,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苦恼。我无法思考,离群索居,终日失魂落魄……,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照基督的吩咐行,那我将在政治圈中成为一个怪人,甚至失去朋友与前途。政治是我的尊严,但基督是我的生命。”在不止息的挣扎里,他没有祈求上帝赐下平安,他祈求上帝赐他正确的选择,为了上帝的旨意,他可以忍受等待时的起伏揣测,以免为平安而平安,而去找一种廉价的、假性的安全感。
八、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在伦敦他不断的到各教会聚会,寻找答案。到了12月,他决定放弃政治;在这关键的时刻,他遇到了约翰.牛顿(John Newton)牧师。约翰.牛顿年轻时是贩卖黑奴的船长,信主后写了许多著名的诗歌,如“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耶稣你名何甘甜”(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等。当威伯福斯夜里来找他时,他六十岁,对威伯福斯苦毒的情绪以及近乎亵渎的言词,没有一句责备。约翰.牛顿知道这个属灵的婴孩,已经听到太多其他基督徒的劝告,也看了很多敬虔的见证,以致于失去了跟随的重心,反而以自己的想法和外在环境来定夺。威伯福斯发现约翰.牛顿听了他一千零一个烦恼后,仍是那么平静,给他一个定心丸。约翰.牛顿认为,也许上帝带领这个年轻人要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从目前的工作中撤退,靠上帝走下去。末了约翰.牛顿为他祷告,“我盼望并且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这个代祷成为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当一个人知道上帝救赎他的目的,那个荣耀感比在罪恶中不断的自责更能振奋人心,使人勇往直前。
九、重回战场
威伯福斯并没有因为约翰.牛顿的劝慰,就回到议院,他仍常独自一人到野外祷告、默想、亲近主。1786年复活节的早晨,有个年轻人释放的在野外大声唱歌、祷告。他事后写着:“田野里的一花一草都与我一起欢唱,我的心中满了感谢与赞美。”他决定要重回议院,并写道:“第一重要的是,我要回到工作中,认识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而不是当逃兵。”十二年后他在《真实的基督教》(Real Christianity)一书中写道:“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作见证,并且义无反顾。”从此,他看议院不再是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地方,而是他的神学院,让他慢慢的学习如何在这个位置上,实践圣经的教导。
十一、道德提升法案
死尸法案虽然一时没有通过,威伯福斯并没有松懈下来。他回到剑桥,开始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科学的书,以弥补过去大学没有努力的科目。他说:“读书有一个好处,在阅读时自己是时间的主人。”此外,他随身携带一本小簿子,记录在人群中所听到、所看到的,他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只是看法,”“我自认是个政治圈里的天路客,我工作的地方可不是青草地,也不是可安歇的水边,而是满了纠缠的荆棘地;我必须常常儆醒与祷告,以严谨的生活自我要求,并以圣洁来分辨上帝的同在。我相信上帝不是以我是多么杰出的政治家来评断我,而是看我深处的意念与本质是否蒙他所喜悦。能对圣灵敏感,起来为某个法案或政治圈的朋友祷告,是他赐给我工作上最的大恩典。”“因此在最困难,或是迷惑时,即使是置身于议院的唇枪舌战中,我也低下头,拿起纸笔记录我的祷告。愿我的政治生涯是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1787年的春天,威伯福斯提出“道德提升法案”,他认为国家政治的革新是由上往下的。无论国王、王后、宰相、主教、法官、议员,愈有权力的人,就需要有愈好的道德,才配维护国家的道德。虽然道德不能改变人心,但是可以减少试探。他提出“法令的执行与订定者,应该过着比较严谨的生活,不该酗酒、辱骂、咒诅、赌博;不该到败坏风纪的地方,不该从事不合法的娱乐。……这些不道德的事看来起都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严格的要求,就能避免大事的偏差。不正确的法律是在小错上马虎宽容,在大错上严刑峻法。”
这个法案引起不少的反对。菲茨威廉(William Wentworth Fitzwilliam)爵士反对说:“在政治、法律里讲道德,只不过是过度敬虔的基督徒先入为主的观念罢了!道德是关在你家里面讲的,不是在外面讲的,在外面谈道德是虚伪的人。在外面需要灵活的运用法律。假如国家当权者讲道德,看吧!国家的财富立刻如泡影消失。”议员笛福(Defoe)也反对:“法律是困住那群软弱的人,一个人权利的多少,就看他能让法律对他莫可奈何有多少。”在众多的反对中,威伯福斯力辩:“政治里的虚伪者不是持守道德的人,而是那一群只要表明一个领袖或主义摇旗呐喊,就可晋身权贵,这种不守法制才是真正的虚伪。所以愈有权力,就愈不守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你们要知道,有权者能逃脱法律的管制,但是对不起上帝的荣耀,因祂托付我们管理,而我们管理的动机却是为了满足自我。没错!我是基督徒,我要将基督徒伦理实行在政治、法律中,因为基督徒应是世界的光,既然在生命上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就该有截然不同的、合上帝心意的提案,而不是使已经混乱道德的法令,更加的混沌。信仰绝对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要影响周围的人。”
这个法案仍然没有通过。但是威伯福斯说:“看吧!我们国家犯罪不断地增加,绝对不是法律订的不够周全,也不是缺乏执法的警力,而是道德降低。这种降低是受从政人员操守的劣化,进而劣化议院,蔓延到社会。我相信英国的命运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到政治性的抉择,或是在关键的时候,愿意顺服基督。因此国家的复兴,乃在乎有政治家,即使很少数也好,愿意回归真实的基督信仰里。”这犹如一具福音炮筒,震出隆隆巨响。有些基督徒政治家开始在议院相聚,组成祷告会。这个祷告会,逐渐形成一个超党派的小团体,号称“阳光协会”(Proclamation Society),宣告一切的政治活动都可以摊在阳光之下,若有任何暗晦不法的活动,欢迎外人揭发。这个团体在1787年年底,发展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八位基督徒政治家,不同的背景、个性、党派、专长,只是因着相同的信仰,一同奋斗三十六年,将人类历史上邪恶的奴隶制度,不流一滴鲜血,不用大炮、步枪,只用法制的改革,挣断了整个奴隶制度。不仅在英国,连当时贩卖黑奴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等国,也因着他们的努力,通通废除黑奴贩卖。大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曾为这批在克拉朋的年轻政治家代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克拉朋位于伦敦的郊区。威伯福斯所提的法案被封杀后,他病了一场,医生诊断是溃疡性的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认为:“顶多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威伯福斯的选区闻讯,都准备要补选新的议员,他的敌手也窃喜那个提倡基督徒伦理的家伙要完蛋了。威伯福斯就在克拉朋购下一座房子休息养病。这时他的信心陷入低潮,怀疑回到政治界事奉上帝,是上帝的呼召,还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啊!除了你的能力以外,没有人的能力、智慧、计谋能够帮助我,我的心急速地奔向你,求你把你的能力赐给你的仆人。哦!主啊,我在极深的困境中,痛苦像座无法忍受的山,压在我身上,愿你怜恤你的仆人,使我重得平静、安息……”长期的等候祷告,还是沮丧痛苦。他的朋友说威伯福斯不是要死了,就是要疯了。上帝好像不听祂仆人的祷告。有一天他祷告:“不是因为失败就自哀自叹、祈求上帝赐成功来坚固我,或以世人的掌声来确定这是你的道路。不!无论成败,无论褒贬,我愿回去尽自己的责任。”这时忽然阳光重现,心中的重担像雾气般地消失了。“有些事情即使是失败了,无论大或小,只要是为上帝而做,必能留下长远的影响。”当他脱离了以世俗成败来衡量上帝旨意之后,上帝才赐给他解救黑奴的重任。他的病也逐渐好转。
这时,开始有些基督徒到他住的地方讨论新法案──“禁止贩卖奴隶法案”(Bill of Slave Trade)。从1784年底到1790年初,有七位年轻的基督徒议员或政治家,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并且约每星期在威伯福斯的家中聚一次,一起探讨奴隶制度的现况。这七个人后来都成为历史上解放黑奴运动的著名人物。
摘自:兄弟相爱撼山河
【蒙校园书房应允转载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