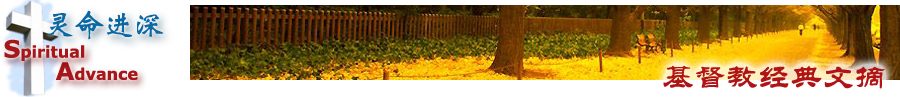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旅行作见证
1731 年,辛生铎夫到哥本哈根去,有机会向丹麦国王和他的宫廷大臣作见证。由于他出身贵族,所以主常藉着他使身居高位者的心意转向神。论到辛生铎夫这一面的工作,施旁恩伯说:
“……圣灵在他里面满有能力,当伯爵把基督的心意向这些人陈明时,他们无法抗拒……。”
有一次,帕勒斯勋爵 (Lord Chamberlain Von Pless) 告诉他:“皇上想跟你谈话当你和皇上谈论时,也该有诚意,显明是神的见证人,正如你在我们间那样。”于是应邀赴王的筵席:
“后来,很多人切切想向他表示推许和爱慕。这类赞誉多得令他厌烦,他很想摆脱。
辛生铎夫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人们争相向我献殷勤,我因而清楚知道,神向我证实,我跟随他的儿子并没有丧失什么。但这只叫我更渴慕回到受苦而蒙福的境地,那里虽有压迫,但却感到泰然安息。’”
丹麦国王对辛生铎夫的印象很好,他想在加冕典礼时授勋给他。辛生铎夫心感为难,不想接受人的荣誉。但皇后的母亲劝他不要拒绝,免得把事情弄僵,他就勉强接受了。施旁恩伯记载说:“然而自此以后,他更坚定的向往基督的羞辱,更勇敢宣扬他的话。”
1731 年 7 月 21 日清早,辛生铎夫结束了这次出外作见证的旅程,回到赫仁护特。
“他发现未婚的弟兄们在一起祷告。又看见他所爱的赫仁护特教会这么兴旺,因此非常喜乐,教会也因着他的返回大得鼓舞。教会不仅在表面上人数加增,各人心里所享的恩典,也是多而又多。聚会的地方增大了一倍,但仍坐满了人。……说到教会,他喜乐的说:“耶稣永远是主,他供给的恩典,常新不旧。’”
当他得知近来有七十四人流亡到赫仁护特时,就在回去后的次日,邀请他们一同用膳。
1736 年,辛生铎夫徒步到德国南部和瑞士一行,目的是向所遇见的人作见证。他途中大都穿着便服,单独前行。他坦诚见主,很多人都愿意接受。
灵恩和神迹
1730 年初,他们跟邻近的团体有交通,这些团体被称为“灵感教会”。因着这些交通,辛生铎夫认识了他们的首领洛克 (John Frederick Rock) 。辛生铎夫很敬重他,认为他严肃庄重、诚恳谦逊。但洛克有一个怪毛病,就是常说预言,并且说的时候身体剧烈震动,头部前后摇摆,速度惊人。其实他所说的预言不过是他个人的意见,但被人加以记录,又交给有关的人。辛生铎夫虽很讨厌这件事,却没有过早下判语。后来他记述:“……我抑制自己,不下判断。这件事必须由它本身显明对错,并由圣灵根据圣经就着这件事有所训诲,那才是判决。”
1732 年,洛克再造访赫仁护特,他的灵感仍使辛生铎夫生厌。恰巧当时“灵感教会”的长老坚持实行擘饼和受浸,而洛克又在其怪异的灵感激动中,蛮横无理的加以反对,这就显明了他灵感的根源是出于那恶者。辛生铎夫随后记载说:“……我不再犹疑,完全拒绝那种灵感。”
此后又有神迹兴起,教会因而受到另一种试验。施旁恩伯记述说:
“那时,在赫仁护特教会中,有些人显明是有各样的恩赐和属灵的能力,而神医却特别多。会众既简单又顺从,因他们相信主说他是垂听祷告的主。每受难题重压,他们便告诉主,希望他来多方解救,而事情往往照着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就了。伯爵为此很喜乐,暗中赞美主俯就眷顾贫穷的和缺乏的。他认为这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乃是圣灵的果子,理当加以珍惜,却不应成为别人绊脚石。他认为弟兄姊妹不应把这些事当作特别,以致过分加以重视。每逢遇到神迹奇事,就如有人伤势危殆或在病中极其痛苦,却因用信心说话或因着祷告,转眼便得到医治,他都把它当作平常,很少提起。他公开或私下又常说,奇迹并非为着信的人,而是为着那些不信的人。有行神迹的信心乃是恩赐,有这恩赐的人并不比神的其他儿女更好,反而可能更不及没有这恩赐又不努力求得这恩赐的人。惟有爱基督、凡事交托他、顺服他旨意的人,才更稳当。因此,他一旦看见有人急切渴慕得着神迹的医治时,便感到疑惑,但也不会加以干涉。”
辛生铎夫认为过于强调神迹会叫人偏离主;教会对此也清楚了,弟兄姊妹们没有因这些事而迷失,却以尝到主的美善为追求的目标。
宗教人士的反对
在赫仁护特以外,有宗教人士起来反对他们。有神职人员出版并派发一封教牧的书信,恶意批评辛生铎夫,指责他是“情绪的奥秘派”,他的教训不健全、不合乎圣经,又认为他的同伴也是奥秘派。
那些曾与辛生铎夫很亲密的敬虔主义者,也开始反对他。在富朗开死后,敬虔主义者产生了一种党派精神,强调特殊的救恩经历,就是必须经过痛苦挣扎才能蒙拯救;他们对其他得救的经历是否正确有所怀疑,而辛生铎夫的得救经历则与他们的模式不符:
“伯爵从年幼就学习经历与基督同在,他的经历与那个模式不同。即使他能有那样的经历,他也反对把神对待人的个别方法,弄成一种统一的格式。他以为信徒与救主的关系是喜乐亲切的,这与他早期的教师的看法不同。”
对于别人的批评,辛生铎夫并不答辩,这是他历来的立场。这一点从以下怀力的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出来:
“对书面公开的攻击,他常以个人名义用信件私下回答作者。即使是公开回答,通常也不是直接回覆,而是一些报导,由他自己或同工撰写,为使普罗大众对摩尔维亚弟兄们有所认识。诚然,他一生尽职,也常被迫解释他的立场,而他卫道的著作内容十分广泛。”
辛生铎夫的态度和主耶稣一样,他不为自己辩护,却宣扬神的真理。他说:
“我向来恨恶与敬畏神的人和热心的教授争论。我不写信,不印发刊物,也不向他们讲什么为自己辩白的话。”对他本人来说,他坚持这个原则,但他的朋友若受到攻击,他却不避免答辩。
教会也该有这种态度,正如辛生铎夫所说:
“保持这种立场的教会,其最明显的特徵乃是敬虔和有信心。真正属于教会的人知道怎样容忍与善待会众和外人。他们严以克己,……自觉不配得神的恩典和所享的自由与祝福。他们带着财宝,却像是借回来的,惟恐轻易失去。他们避开逼迫,因免受迫害而感欣慰。但逼迫若临近,他们也屹立不动,勇敢面对。”
政治的敌挡和被放逐
宗教人士不仅用话语反对辛生铎夫,他们更因着嫉妒和猜疑,唆使政府来抵挡他。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作两方面的调查:一、那些移民是否被怂恿、受引诱而离开摩尔维亚;二、赫仁护特教会有什么教条和实行,引起那么多的反对。
政府在 1732 年进行调查,施旁恩伯这样记载:
“首席地方官召见每个移民,要他们讲述为何离乡别井,以及他们所受的逼迫和对救恩的盼望 ( 当时有四十多位见证人出席 ) 。他们的态度真诚,令人信服,各委员都大受感动。”
调查的结果,委员会发觉一切均正常。伯爵随后决定不再收留移民,一则因为有两位弟兄返回摩尔维亚帮助他人移民,但却因此而丧生;二则因为德皇实行新政策,禁止摩尔维亚人移民。
政府的抵挡虽平静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又转趋猛烈,甚至在 1736 年下令放逐辛生铎夫。他被控诱使佃户离开原来地主的地土,以扩大自己的组织,因而被命令立刻离开赫仁护特。实际上他是被控“偷羊”。辛生铎夫有这样的反应:
“那是无关紧要的。十年内我不能回到赫仁护特,因为时候已到,我要出外召集流荡的信徒,并到普天下传扬救主。主在某一段时期需要我们到某一特定的地方作工,而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伯爵离开后,弟兄们对教会中的事务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了一致的决定:
“第一、不可受引诱作违背良心和抗拒圣灵的事。第二、要防备奇特的意见,并遵守圣经中最简单而基本的真理;凡不遵照神真理而行的都不得参与其事。第三、慎防分裂。”
伯爵离开赫仁护特后,他鼓励家人和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无论居住在那里,都该在一起聚会、唱诗、祷告和花功夫读神的话,像往常在赫仁护特时那样。辛生铎夫以为,主日、假期和每天的聚会,当照主所设立的继续下去。
政府后来颁布了一道宽容训令,对赫仁护特教会有利,但宽容的范围有限,并且执行的日期耽延了很久。政府在 1736 年对赫仁护特进行了另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一切仍然井井有条。施旁恩伯这样记述:
“委员会轻易地查明了真相,因此委员在离开时公开为教会作证说:‘你的行为诚实并且通过了试验,清白无罪。’但虽经详细调查,其决议却在十五个月后才公布。”
政府终于公布决议,赫仁护特确实获得认可,但没有提到辛生铎夫被放逐的事;他虽身为伯爵,却仍要过着放逐流荡的日子。
辛生铎夫于 1732 年离开赫仁护特,他决意过流荡的生活。施旁恩伯有以下记载:
“伯爵一离开他的土地,就决意不为自己保留世物;他到处为家,看自己如在世上的客旅。他本可成为很多产业的地主,但却认为在世为主漂泊更好。他说:‘我知道,按着本性我和别人一样,喜欢在家居住,并且极想留在故土。在家时自然会想到有许多事要作,也能好好利用时间,但主不喜欢我这样过生活。我效法他的榜样,经历到处为家的喜乐。当他还在襁褓中,就被逼离开安息之所,到处奔波。’
‘主管理我们的一切。无论何时,他按着自己的智慧,把我们放在某一境地,即使是在旷野,也会使我们有归家之感。’”
到赫仁哈格开拓
辛生铎夫动身离开后不久,内心突有所感,他说:
“在旅途中,我灵复苏,因主的眼目引导我。我无需立志或定意,却能劳苦作工,事事成就。”
与伯爵同行的人,他称之为“战士团”或“漂泊者联会”。他们首先到达朗尼堡 (Ronnoburg) 的马利安邦城堡 (Marienborn Castle) ,该处位于威特尔维亚 (Wetteravia) 的诸侯国境内,在赫仁护特以西,靠近德国的西面边界。他们在那里居留,以赫仁护特为模型, 加以开拓,定名为赫仁哈格 (Herrnhage) 。下面一段引文描述那里的团体生活:
“未婚的弟兄姊妹们,分别住在诗班房舍中,凡物大都公用,并且随时准备为主效劳。没有人……单单为自己作工。他们都有工作,以确保众人皆无所缺。同时人人接受训练,得到装备,成为‘战士’。辛生铎夫说:‘不论在那里,弟兄们都当切实合群,不求私,只为全教会获益而努力作工。这是很要紧的。’”
不久,赫仁哈格的会众日益增多,这可从下文得知:
“那一年, 从英国、挪威、丹麦、荷兰、立凡尼亚 (Livonia) 、 瑞士以及德国各处,都有人来,使赫仁哈格人口加增,愈发兴旺。”
但是辛生铎夫对人们聚集到赫仁哈格这事并不感高兴,他更愿意他在原居地随时为主作见证,使欧洲各处有较多作主见证的金灯台。
约翰卫斯理到访
1738 年,约翰卫斯理到漂泊者聚居地探访,觉得很好,他这样报导:
“我来到这里的教会中,会众彼此交谈,如同在天上……。他们既同有一位主,一个信仰,因而同享一位灵;有灵的温柔和仁爱,使他们说话一致,满了活力。”
在探访期间,他引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来形容所看到的光景:
“弟兄合一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凡对主耶稣基督真有一点爱慕的人,他们都加以爱护。”
他写信给弟弟说:
“弟兄们的灵实在好,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的。无论老少,随时随地所谈论交通的尽是信心和慈爱。我……努力……效法这样荣美的榜样。”
卫斯理又表示,他切慕留下与这些摩尔维亚弟兄们同住:
“我甘愿一生住在这里。……这样好的基督教何时才能遍布全地,像海洋充满了水呢?”
遍游欧洲
辛生铎夫除了在赫仁哈格负起一些职责之外,还有负担更多外出,遍及全欧。他想去探访那些散居的弟兄姊妹们;他称他们为“散居国外的犹太人”。他到过英国、荷兰、柏林、瑞士、法兰克福,后来甚至到了俄国。在英国,他设法召集弟兄姊妹,如同把羊召聚为一群。施旁恩伯这样记载:
“有几个人因参加伯爵家里的家庭崇拜而蒙福,也叫别人一同得福。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存心单纯,倚靠主,合而为一,又接纳了伯爵所定的几个规则。他们在那些规则上签了名,规则的各点如下:
一、我们只相信并实行圣经所清楚讲明的,不论是否合乎我们的想法和意见,我们都加以相信和教导。
二、我们要单纯如孩童,彼此交通,互相联结。为此我们每周聚集一次。会中只祷告和读经,大家因而得着造就。对于能引起争论和分歧的事,即使是极微细的,都一概不提。
三、我们坦诚相向,彼此直言不讳,对每个人的错处都毫不隐瞒,免得有人把别人看得过高。
四、我们按着所得恩赐彼此服事。各人平静安稳,准备好在人群中为主作工。
五、我们不干预任何教理或教务的事,却只注意三件简单的事,就是藉耶稣的血得救并成圣,以及彼此真诚相爱。”
伯爵在柏林遭遇反对。他想在那里站讲台,但被神职人员暗中排挤,他便把自己的房子开放,来者不拒。
“开头的时候,前来聚会的只有几个人。他们说明来意,因他们认为伯爵是按照在主耶稣里面的真理而诚实作见证的人。聚会起先是在伯爵自己的房间举行,但不久因需要较多空间,就不得不使用前厅。到了前厅也不够用时,他决定连楼上也开放了,这样就可容纳几百人聚会。起初,他不分男女,同时向他们传道。但当人数大增,甚至连楼上也容不下时,他便将会众分为两批,逢周日和周三向男界传道,逢周一和周四向女界传道。为了节省空间,从一开始就不设座位,所有赴会的人,不论是有地位的或是贫苦卑微的,都得站着听道,并无分别。一天,有人点算他门前的马车,计有四十二部之多。”
在法兰克福,德国诗人歌德 (Goethe) 的母亲也参加了漂泊者聚会。虽然歌德不是他们的成员,但也是常客。“辛生铎夫认为,他这次留在法兰克福的时间虽短,却是他一生工作中最令他满足的经历之一。”
后来,伯爵到俄国后被监禁。在被囚期间,他写信给妻子,内容如下:
“我虽然被捕,但你千万不要担心。 我保证在这里很喜乐。想起能我们的宝贝的儿子,也使我喜乐。若非主的旨意,这事断不会发生。虽然已有很多先兆,但我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写信给副首相和拉西 (Lascy) 伯爵,以致自投罗网。神所作的都有他的目的,我确信主所作的事事周到。官长非常有礼,我看他别无二心,全是善意。请多记念我。如今有少数基督徒为主被囚,他们因有天父同在,即使遭受这样的事也感欢乐。我会尽量多写信给你,使你知道这里的情形。亲爱的,请记得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都在他信实的手中。他的引领满有恩典和祝福,但有时却似乎很奇特。若让我们来决定,我们会拣选另一条路。我一生绝没有想到我会被囚,但现在事到临头,我却感非常满足。我所要告诉你的,以前都已说过了,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只是当我不在的时候,你该加倍努力,替我尽职。”
辛生铎夫伯爵这次外出,又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Frederick William I) 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此后多年,友情弥笃。普鲁士王居于柏林,他鼓励辛生铎夫在他的国内不偏不倚的传讲神言。辛生铎夫在柏林的讲章刊印流传,后世认为那可算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西印度群岛之行
关于辛生铎夫西印度群岛之行,路易斯 (Lewis) 有如下记述:
“伯爵不宜坐船,但他以一贯直截了当的方法加以克服。他后来记述:‘要办的事既多,我便对主说,生病对我很不方便。因此在启航前,我的身体便好了。’抵达西印度群岛后,他对传教士所受的待遇大感愤怒。他写信回家对妻子说:‘我大发雷霆,冲入城堡。’”
总督不仅亲自向辛生铎夫道歉,释放了囚徒,还答应保障他们的安全,不受逼迫,又保证他们可随意自由传道崇拜。有八百个黑人愿听福音,伯爵说:“在圣多马 (St.Thomas) 的神迹比在赫仁护特的更大。’”
在往返圣多马途中,伯爵写了几首他作品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诗歌,“救主的宝血与公义”就是其中一首。下面两节道出辛生铎夫一生获得动力的来源:
救主宝血与他公义,
是我美丽,是我锦衣,
在他面前当他来时,
有此盛装,我无羞耻。
你的降生、受创、受死,
我要承认若有气息,
直到那日与你见面,
以你公义作我装饰。
他从西印度群岛回去后,知道女儿已死。不久他自己也病了。
美洲之行
1741 年,伯爵内心有催促,要再去美洲看望那里的弟兄姊妹,这次的行程由 1741 年起到 1743 年止。因他要离开几年,所以他在赫仁哈格的职务由谁担当便成了问题。经过多次祷告,多方考虑,众人认定基督乃是他们的大牧长,无人能代替他。怀力说:
“经过这件事,摩尔维亚的教会蒙了拯救,没有产生属灵上的教皇制度。在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心目中,个人每天与主交通乃是宗教生活的要素。按真理,教会从起初就以耶稣为元首……。”
到了美洲,他要人称他为路威 (Ludwing) 弟兄,而不是辛生铎夫伯爵。他把当地一些显要请来,其中有富兰克林 ( Benjamin Franklin) ,当众宣布放弃伯爵称号。
辛生铎夫很关心印第安人,感到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到三个不同的印第安人部落探访,但有些印第安人对他有敌意。从下面一段记载他到雪里族人 (Shawness) 那里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所受的敌视:
“们认为辛生铎夫是骗子和盗贼,图谋开采他们境内的银矿。他三次幸免于难:头一次险遭剥去头皮;另一次差点被毒蛇所咬;再一次因马鞍断开,他从马背掉进河湾里,几乎溺毙。这些危险的遭遇非属意外,无怪他报导说,雪里族人完全无知,对基督徒不善……。
艾鲁括斯 (Iroquosis) 的六族印第安人却欢迎他,当各酋长到费城重订盟约时,伯爵带着神的权能去见他们。他表明并无意抢夺他们的土地,却诚心要把救主传给他们。酋长们相信了他的话,结果,他们欢迎伯爵到他那里探访。
他对印第安人的盼望日增,因而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接续他去探访。
基督徒在美洲英属殖民地里分裂的情况令辛生铎夫很纳闷。他觉得他到美洲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着信徒的合一而工作。他曾经七次召聚弟兄姊妹在一起,盼望他们合一。怀力说:
“伯爵劝勉他们不要争执,反要在爱里商讨最重要的信条,从而看见彼此在基本信仰上是极为接近的。至于那些无关紧要又与救恩无碍的道理,彼此可在爱里互相包容。”
关于那七次聚会,怀力说:
“这些聚集平均出席人数超过一百人,而其中约有半数是受委派的代表。宾夕凡尼亚州的各宗各派都有派代表或宾客参加头三次会议。其中包括路德宗 (Lutherans) 、改革门诺派 (Reformed Mennonites) 、史文克斐派 (Schwenkfelders) 、第七日浸信派 (Seven-Day Baptists) 、分离派 (Separatists ,脱离教会的一班人,自成一派 ) 、隐逸派 (Hermits) 和摩尔维亚的信徒等代表。虽然这些集会基本上是德裔的聚集,但圣公会、 长老会和贵格会 ( Quakers ) 都有宾客出席。”
辛生铎夫虽已尽了全力,却不能达成使他们实行合一的愿望。
当辛生铎夫在宾州时,他走访各处信徒聚居地,花功夫牧养他们。他给其中一群摩尔维亚信徒起名为“伯利恒”,并在那里劳苦作工,那里的教会大蒙恩惠,开始兴旺。有人接到安娜尼赤曼 ( Anna Nitchmann ) 的来信,里面说:
“我们在‘伯利恒’的喜乐非笔墨所能形容。有生以来,我从没有像在这里那样喜乐过。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月之久。当时,弟兄姊妹都搬到那里,组成了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如小孩一般。神的羔羊把我们这班罪人作成蒙恩的儿女。”
在这段期间,辛生铎夫出版了一本诗集,由富兰克林印行。
美洲内地的邮递服务创始于两个摩尔维亚信徒居住的城镇。那两个镇是伯利恒和德裔城 (Germantown) ,而信件起初是由人步行传递的。
在美国聚居的信徒中,有一种实行为人所乐道,那就是辛生铎夫打发弟兄姊妹到各处作福音的渔夫。
辛生铎夫的晚年
在他返回欧洲的途中,遇上了猛烈的风暴,船长和船员都很害怕,以为要丧命了。虽然辛生铎夫笑容依旧,语带安慰,却未能稍减他们的恐惧。辛生铎夫便告诉船长,风暴会在两个钟头内停止。时限到了,他叫船长走上甲板,风暴果然在几分钟内停止了。船长记述后来所发生的事:
“……我下到船舱,告诉伯爵风暴已经停止,我们已脱离险境。他随即要我们和他一起感谢神,因他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照他所说的,都感谢神。
我很想知道伯爵怎么能准确的断定风暴停止的时间,于是去问他。我表明不会滥用他所说的方法图利,他相信我的话,并说他会把情由坦诚相告。
他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危难逼近,我首先自省,看自己有无可责之处,若有什么事是主所不悦的,我立刻服在他的脚前,求他赦免。慈爱的主就叫我感到他的宽恕,并且通常让我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他若不愿让我知道什么,我就仍旧安静,并意会若不知道结果会更好。这一次,他却叫我知道风暴会在两个钟头内停止。’
照他所说的看来,神──我们的救主──竟然这样俯就人,又把秘密告诉人,我觉得很新奇。我从前常听人说神是伟大的、震怒的、忌邪的,却很少听人说他对人有测不透的爱,还肯俯就我们这些可怜的受造者。但我相信他所说的,而且对这事的真实性毫不怀疑。因与伯爵同船,我可耳闻目睹他的言行,心中清楚知道他确是耶稣基督的忠仆。”
留在英国
1749 年至 1755 年间,辛生铎夫住在英国,那里的弟兄姊妹照他所愿的只称他为门徒。当时全英国约有两万处的聚会。辛生铎夫抵达后便到伦敦的弗德巷会社 (Fetter Lane Society) 访问。卫斯理在几年前便已加入了那个团体,他记述参加其中一次聚会的情况:“我到艾德其街 (Aldersgate Street ) 的一个会所,不过我是很不情愿去的。当时那里有人正诵读路德所写罗马书的序言。约在八时三刻,那人讲论到人因信基督,神在人心里作工,叫他有了改变。我听了之后内心感到非常温暖,觉得自己已确信基督,只有他是我的拯救。我有把握他已除去我的罪愆,连我也被除掉了,他已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可是辛生铎夫留在英国的这段日子并不轻松愉快,反而经历了很多内心的对付。这段日子后人常称之为炼净期。当时摩尔维亚弟兄们多走向极端,宝爱基督的苦难,并愿效法他过受苦的生活。
经济困难
当时辛生铎夫又遇上经济方面的困难。他向来都乐于将所有的收入毫无保留的布施给人,因此当自己有所需时,便常常无钱应付。对于钱财,他早年已养成了这种态度: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叫他欣慰。他六岁那年,第一次从别人手中接受金钱,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个试验;他并未把钱留下,而是把它给了头一个遇到的人。他特别喜欢施惠与人,此种性情终生不渝。当别人有需要而他却无法帮助时,便会深感伤痛。他若觉得别人比他更有需要,就会倾囊相助。每逢施惠给人,他总带着乐意的态度,叫接受他恩惠的人觉得自己是被欢迎的,且是他所喜悦的。……他自己一点也不奢侈。他感到必须克己才能有更多可以给人。总而言之,从年幼起,他便对每个人都满了爱和同情,不管别人如何自私……。”
由于弟兄姊妹、欧洲众教会和世界各地的工作都有需要,辛生铎夫在荷兰和英国举债,濒临破产,几乎被关进钱债监狱。后来得弟兄们调解,并把教会的财务处理妥当。自此,他们觉得有需要把辛生铎夫的财产和教会的分开。事后证实那是明智之举,并且解决了当时的难题。
卫斯理和怀特斐的反对
后来约翰卫斯理与弟兄们断绝了联系,更称他们为讲异端的,是骗子。卫斯理曾赞赏弟兄们,也得过他们的帮助,但后来对他们却这样决绝,这是难以理解的。可以猜想得到,辛生铎夫必因此而心如刀割。卫斯理抨击摩尔维亚弟兄们所发表的一些偏激的言论,弟兄们后来也为此而后悔。但是那些讲论不过表明他们热切爱主,渴望与主联合为一。卫斯理却“请大家注意,他们近来极力强调基督的创伤,并请所有受愚弄而与弟兄们为伍的人,与他们断绝交往。”
其后怀特斐也反对弟兄们。 他曾向摩尔维亚弟兄们求助,在美国建立孤儿院。他们乐意给予协助,但后来他也像卫斯理那样离弃了他们。
“……怀特斐与弟兄们维持了较长 ( 较卫斯理 ) 的友谊,甚至请他们帮助他在乔治亚州建立孤儿院……,但他也逐渐与他们疏远,最终更在弟兄们备受反对的时候,写了一封公开信,其中满了悲慎,指责伯爵。
当伯爵住在伦敦附近的林赛大楼 (Lindsey House) 的时候,英国枢密院总理格兰维尔勋爵 (Lord Granville) 曾写信给他说:‘你若控告怀特斐,一定可以胜诉,因为根据英国法律,他应受制裁。’但伯爵回信说,他不能下此决心。反对派不顾脸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公开印发对弟兄们的评论。伯爵若采取行动对付他们,很多人的前途可能就此被毁。但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要学主的样式,所以无意靠官府 ( 或法庭 ) 躲避可能临到的苦难。至于怀特斐,仍有很多人因听从他而受益;故此,他不会写什么有损他名誉的东西。事情就这样了结。”
辛生铎夫离去后,摩尔维亚弟兄们正式采用“弟兄联合会”这个名称,他们成了其他基督教团体之外的另一个组织。辛生铎夫向来反对成立组织,但当他从美国回去后,反对已经太迟了。在他外出的期间,他们已把名称改定了。
丧 子
1752 年辛生铎夫经历了另一场试验,就是他儿子去世了,这事令他很失望。 ( 十年前,他四岁的儿子大卫和五岁的女儿莎乐美已死去。 ) 这儿子名叫朗尼德斯 (Christian Renatus) ,死于肺病,年仅二十四。 他寿数虽短,却写了一些诗歌,其中两首的题目的“救赎主满带忧苦,为我上橄榄山”和“有分在基督里是最大的福祉和需要”。辛生铎夫曾盼望这个儿子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与摩尔维亚弟兄们同工。
“照我们所见所闻,伯爵与基督的关系向来密切,这使他视生死如一,无论何者他都全心接受。丧子数周后,他告诉同工,关于孩子们,他很久前已与主立约──‘孩子们出生那刻起,他就不把他们据为己有,却把他们完全交托给主,作为他的产业。’但他极其伤痛,写信给会众说:‘我不明白这件事……以后神会叫各人心里明白。’施旁恩伯对这事有深入的观察:
当儿子的父亲在迈恩 (Mile End) 时,有人把儿子的死讯带给他。我真难描述他的感受,我只能说,事后他常追述他儿子对他何等重要,言谈间眼中充满悲哀和感激。但谈到他看过儿子每天与主交通的笔记时,他的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从那些笔记中,他看出儿子爱主之情何等柔顺热切,他保持与主的交通是何等亲密。朗尼德斯之死令多人流泪;不仅是他的亲人,连教会中的每个人也都流泪,因为他是众人所爱的。”
撤销放逐令
几年后当国王访问赫仁护特时,撤销了某些对辛生铎夫和赫仁护特的禁令。怀力有如下的记述:
“萨森尼 (Saxony) 的实情终获得表白,赫仁护特工艺兴旺,农田肥沃,居民的生活井然有序,这些都是实行敬虔生活的结果,见证明确,不容忽视。其他的国家元首也大力推许弟兄们,其中以普鲁士皇弗德列 (Frederick) 最突出;德斯登的官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被放逐的伯爵之为人。”
官府终于撤销了放逐令,辛生铎夫可以自由返国。结果他在 1755 年回家。
此后他仍有负担继续访问分散的弟兄姊妹,并以此为主要的工作。在他赴美之前,有以下的的言论,公之于众,说明他此行的目的:
“我领受了主的托付,不顾后果的去传扬耶稣流血受死的信息。在我认识摩尔维亚弟兄们之前,早已蒙了这样的呼召。我向来与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关系密切,现在仍是如此。他们全心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又邀请我和其他弟兄们服事他们,彼此交通。”因着辛生铎夫在海外劳苦的工作,所以在赫仁护特成立二十年后,各地有七处类似的信徒聚居地出现,还成立了各种布道团,其中有四处在德国,一处丹麦,一处在荷兰,还有一处在美国,不过教会生活尚无法扩展到俄国;然而在波罗的海一带,散居的信徒约有七千,相当于摩尔维亚弟兄们总数的三分之一。
丧 妻
1756 年,辛生铎夫的妻子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施旁恩伯记载这事如下:
“ 6 月 19 日,伯爵所爱的妻子出席会议,第一段完后,她也走完人生的旅程。她安然睡了。她的一生值得称许,死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病痛。不仅赫仁护特教会,连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件事都感慨良深,难得有人不热泪盈眶。但没有人比伯爵更伤痛,因他最能体会这三十四年来妻子如何从旁帮助他。他不理自己对妻子去世的哀伤有多深,仍去安慰别人。他不阻止多人为她洒泪,因为那是发自由衷的爱意和恭谨的感激,她也该受尊敬。主耶稣也曾在拉撒路墓前哭泣,看见的人都推断说,主必定爱他极深。但他提醒众人,主必已考虑周详,知道什么是教会所需和对教会有好处的。他亲自来拆毁,把她接去。”辛生铎夫流了很多眼泪,并对妻子的死亡感到有几分懊悔。
“伯爵现在反省, 他怎样才能在神把他的妻子接去这种境况中得到最大的益处。他花时间在主面前考量三十四年来的婚姻生活。这些年间他经历神的恩惠,使他深感一无可夸,更叫他忧伤的是发现了他自己所犯的错误。他虽觉得对妻子非常忠诚,但他并不满意,因为有时很多事他没法兼顾;若按着基督的心思而活,那些事却应顾到。他在主面前为此惋惜流泪,求主完全的赦免。”
辛生铎夫之死
“辛生铎夫丧妻四年后,即 1760 年,他也去世了,死时六十岁。他因不断到各处去,旅途劳顿,带病多月,终于逝世。虽在病中,他仍常有活动。临终前,病榻周围有人相伴,他对其中一人说:‘基督向父祷告,叫门徒都合而为一,这祷告竟在我们中间实现了,使我们又喜乐又蒙福。这件事你预料得到吗?’他谈到这事时,面上满了慈祥。”
他回顾主藉着摩尔维亚弟兄们所作的工:
“他转向大卫尼赤曼说:‘开头你有没有想过,主会在摩尔维亚弟兄们聚居地,在各宗各派神的儿女中以及在外邦人中间多方作工,像现在我们所眼见的那么多?最初我只求他在外邦人中得着几个初熟的果子,但现在却有成千上万。尼赤曼,我们教会中的信徒人数极多,成群结队的围绕着羔羊站立!’ 5 月 9 日清早,他以微弱的声音向维特威 (John de Watteville) 说:‘我儿阿!我现在要到主那里去。我已经预备好了,他若不愿意在地上再使用我,我就准备到他那里去。’‘主若不愿意,信徒不会离世。这虽有损失,却无妨碍。我也要离去了──但将来必有益处……。”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