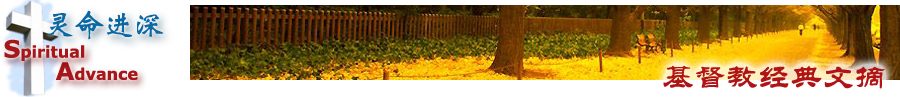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辛生铎夫小传(一)
引 言
莫尔维亚教会的复兴是近代教会复兴的主流,神使用辛生铎夫,使各处因信仰遭受逼迫的热心信徒,由争议、分党的光景,藉他与同工们的祷告、忍耐、等候及生命的见证,带进合一,圣灵浇灌的光景中。他们在小组交通、敬拜赞美,二十四小时守望祷告(持续一百年),及海外宣教上都作了众教会的榜样。尤其是海外宣教见证,带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教会宣教运动,引发教会近二千年来最大的宣教运动。他的小传可做教会复兴的蓝本。有关莫尔维亚教会复兴史,可参“当圣灵降临”一书。求主兴起更多祷告带进教会复兴。
在教会复兴史中,我们常听人提起辛生铎夫(Zinnendorf , Nicolaus Ludwig)这个名字,但我们对他的认识,恐怕只是一鳞半爪。最近我们收到芝加哥教会出版的“初熟的果子”(The Firstfruit)季刊,其中连载复兴的简史,有五次是说到辛生铎夫的生平。
童 年
辛生铎夫在1700年5月26日出生,他父亲这样记述:
“……星期三晚,大约六时左右,全能的神在祝福我,赐给我第一个儿子。但愿满有怜悯的神掌管这孩子的心,使他行善的路,无可指摘,不容恶占有他,使他所行的路,因神的话而得坚固。”
辛生铎夫是奥地利的贵族,父亲是高级官员,但当他只有四周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起初他由外祖母照顾,后来交由姨妈抚养。
他早期由外祖母养育,并深受她的影响。外祖母能读希伯来及希腊文圣经,又大力支持敬虔派信徒,常在家中接待他们;其中有敬虔派运动的领袖施本尔(Spener)和富朗开(Francke)。
六岁那年,辛生铎夫被主感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他曾有这样的记述:
“我敬爱外祖母,当我与她同住期间,有两件事决定了我的一生。一件事是:六岁那年,我的家庭教师爱德林先生在我家教了三年后要离开了,他临走时对我说了些关于救主和他的美德的话,说到我该怎样才能属于他,并且只属于他。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切、生动的印象,使我哭了很久。在哭的时候,我确实地决定一生只为他而活,因他已为我舍己。另一件事是:我亲爱的韩莉达姨妈对我非常慈祥,常向我讲说有关福音的事。我一心一意听她说话,又和她一同把我的情形带到主面前祷告。……我把自己所有的事,不管好坏,都毫不隐瞒的告诉她。我向她敞开、坦率的交通,使我获得极大的帮助,令我永志难忘。我们在思想与感受方面,都有隐密的交通,这促使我以后热衷于建立一些团体,为着圣徒彼此切磋和启发。”
在了解辛生铎夫的人中,没有人比得上施旁恩伯(Spangenberg) 。他认为辛生铎夫一生有三大准则,支配他过基督徒的生活,而那些准则是在他童年时就已植根在他里面,并且不断增强,直到他离世那天。
“……他对耶稣的受苦和美德感受至深;主既为他舍命,他坚决定意要完全属于他;因此他与密友交通时,总是持坦率与毫不保留的态度。”
辛氏九岁那年便盼望与基督有活的联结。他后来这样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的心从没有爱慕过主以外的东西。”他喜欢谈到救主,也喜欢听见关于主的事。施旁恩伯引述辛氏童年的亲笔记录:
“我幼年就能经历到救主铭刻的感受,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乐事。自此以后,我所有的希望和意愿都向他而去,他是我魂的爱人,他为我赎罪,我要向他而活。虽然我年纪还小,但已开始爱主,他也满足了我的意愿。我听见他在我心中多次说话,又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他。”在日内瓦(Geneva)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我小时的情景,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学我那样作。当年我听见创造我的主竟来成为人,就深受感动。我想:『即或有一天无人再爱主、敬主,我仍要紧靠着他,与他同活同死。』多年来,我和他就是这样彼此倾心吐意,交通无间。我与他交谈多时,如同密友。我多次在房间踱步,浸沉在默想中,我与主单独交谈,感到非常快乐。感谢主,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就已永远顾念我了。但我并不完全明白他所经历的苦难是何等深重全备,配得颂扬;而我的卑鄙和无能虽然是至为明显,但我却不完全明了。我也曾试过竭尽所能去得着救恩。但那大日子终于来到。那天,创造的主竟为我受苦的这件事叫我深受感动,我因而流泪成河,加倍亲近他,与他联结。一人独处时,我便不断与他交通。这样,五十多年来,我跟他谈话,就如亲眼见他一样,天天如此,快乐日增。”
入学受教育
敬虔派对辛生铎夫的影响很大。敬虔派想破除传统基督教的死沉,他们因爱神而彼此相爱,照着信仰而生活,并且坚持个人必须对基督有主观经历,而非仅有知识而已。为了过单纯圣洁、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不上歌剧院、不跳舞、不玩纸牌、素衣淡食。他们相信所有信徒都能尽祭司的职分,他们在家里有小聚会,一起祷告、读经、彼此交通。这对辛生铎夫影响深远,他终其一生就是维护并发扬这些信仰和实行。
辛生铎夫早年(1710-1716)在哈勒(Halle)的藩达干受教育。 哈勒位于来比锡西北三十哩,是敬虔派的中心地,而富朗开是哈勒大学的神学教授,又是藩达干的校长。
辛氏的母亲送他上学时和富朗开谈到他的儿子,使他对辛生铎夫有了偏见:
“她形容她的儿子才华出众,但必须严加管教,否则便会骄傲、自恃。于是年轻的辛生铎夫开始受富朗开的管教,以后每逢他惹到甚么麻烦,校长总是针对他。过了三年多,富朗开才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
以下是一个例子:
“富朗开与一位同事通信,说到他曾慎重考虑要把辛氏送回家去,因为发觉他很难办。他们信中提到辛氏不顺从、说谎、虚伪、爱虚荣、制造麻烦。”
有一位导师也给辛氏不少烦恼:
“这位导师很难相处,甚至不惜巧施奸计为难他。”不过学校对辛生铎夫也有好的影响,他说:
“在富朗开教授家中每天都有聚会,说到基督的国度,叫我很得启发,……我认识了几位传教士、各种遭放逐的囚犯,……那位神的仆人为主作工,满有喜乐;再加上各样重大试炼,凡此种种大大加强了我走主道路的热心……。”
求学成为十字架
为了使他谦卑下来,学校一开始就把他安排在低于他以往已能读到的班级,要他做卑下工作,又因微小的过失惩罚他,不但施加体罚,更羞辱他,例如在他头上挂上假驴耳,叫他站在全班面前。有一次他又被嘲弄,他用拉丁话回答说:“这些羞辱不会将我压倒,反而叫我振作起来。”
虽受到种种无理对待,辛生铎夫却在学业上大有进步:
“事实证明他的学习能力远超过一般学生,但他不大晓得去应用。施旁恩伯说他读书并不很热切,只为了尽责任。他脑海里充满了宗教的事,以致并不把学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不过,他的进步也令人满意,甚至多门学科的成绩优异。他的希腊文读得很好,读新约圣经及希腊古典作品是轻而易举的事。十六岁时,已可以用希腊文演讲。他学习拉丁文的进步更快。给他任何练习题目,他都能即时用拉丁文流畅演说。他说法文就像说母语(德文)那样自然。他读了三年希伯来文,成绩却不好,但在诗学上却甚为突出。他有作诗的天才,灵感如泉涌,往往来不及写在纸上,这个恩赐一生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童年时对主的渴慕,在早年求学期间还持续不断。他关心同学的情况,也想组织青年团体,为要广传福音。他喜欢向同学说到救主,但有时没有讲说对象,便对椅子或其他物件讲说他如何爱主。他年纪虽小,但他说:“我所爱的只有他,只有他。”
“辛氏自小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与救主亲密交往,顺服他的话,如奴仆一样,并且往普天下去传扬他,但不是呆板的传扬,而是藉着圣灵的光照和大能,除去一切阻碍,叫救主能进入人心。”
一生见证他不断否认己,他在这一面有丰富的经历。施旁恩伯说,他心中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就是爱主、爱弟兄,这爱使他每次的奉献都是喜乐、轻省的。在哈勒完成学业时,他讲了一篇告别辞,题目是:“有学识者好争辩之性格”,这篇讲词的主题--基督徒的合一--成了他终生的负担。
进大学
1716年,辛生铎夫进威丁堡大学读书,直到1719年为止。威丁堡是宗教革命的发源地,辛氏到那里的时候,人们正准备庆祝路德在威丁堡教堂大门钉上九十五条罪状二百周年纪念。注册入学后,他一心想读神学,但他的监护人不同意,一定要他选一门将来可以为国家服务的学科,他因而主修法律。在大学读书期间,他仍一直读希腊文新约。
十八岁那年,他曾为哈勒大学和威丁堡大学的信徒合一而奔走,但失败了。当时哈勒大学代表敬虔派,而威丁堡大学则属于路德宗。
期间,他的灵命不断增长。他每天读主的话,宝贝路德和敬虔派的著作。他用很多时间研究诗歌,定时间祷告,又用主日钻研圣经。施旁恩伯说:
“他每天都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祷告,也为公开或暗中与他为敌的人祷告。”
施旁恩伯又说他定期整晚祈祷,整天禁食:
认为应该偶尔整晚祈祷或默想神的话。所以他不顾自己的软弱,定意每周五禁食,并严格坚守了三个月。但常因访客或其他事物而受搅扰,他就改在主日禁食,谢绝一切不必要的访客,全心祷告和默想圣经,因而得着造就。”
他又找机会召集同学在一起,鼓励他们爱主、追求主。为此他发起成立一个小组,名叫“芥菜种”:
员许愿忠于并遵照主的教训,彼此相爱,远避跳舞、赌博等世俗的事,常为他人求福,更特别努力作工,带领犹太人和异教徒归主。组员都戴指环,其上刻有希腊文:不为自己活。”
游历欧洲
当时贵族子弟受教育,必须游历欧洲大陆。辛生铎夫在1719-1720年间周游欧洲。当他经过杜塞多夫城的时候,他向主祈求更多交通于他得苦难。他在荷兰接触到更正教的神学家和其他不属更正教的基督徒,因而清楚看到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里是联合为一的。
在法国,他遇见枢机主教诺爱立(Noailes)辛氏后来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论文给他,论到基督作我们的义的功劳,他写道:
“神若来审判罪人,人惟有藉着信,在主的宝血之上,得着耶稣为义,才能站住。我们得救不是由于教皇或任何人,却完全在于基督的功劳。”
因他们都爱主,所以他感到与这位红衣主教的关系很密切。
游览巴黎时,他对一般旅游胜地不感兴趣:
“附近的凡尔赛有不少宏伟的建筑物和花园,但他到那里只看了几小时就觉得够了。反而在Dieu酒店内有千百个病人得到照顾,叫他深受感动。”
辛氏在巴黎住了不久,但却很不寻常。他说:
“我周游四方,但我多踏足世界,基督却更坚定的保守我。我寻找这世界的大人物,对他们述说救主的恩慈和美善。我遇见他们往往是在意料之外的。对那些不可信托的人,我很有礼貌;对那些热衷于引诱我的,我保守自己,并且一有机会就纠正他们,像我在大学时一样。当日所结的果子,我现在仍然得享。我与主商量每一件重要的事,世界对我没有影响,因为虽然外表上我和别人没有分别,但我在巴黎不跳舞、不玩纸牌。许多认识我的人,认为我已诚心奉献,其他不太明白我的,就说我是敬虔派;但真正称为敬虔派的人,却认为我并不合格。”
施旁恩伯说:
“他的言行表明他反对一种想法,就是居高位的信徒能比别的基督徒更自由。他坚守习惯,继续在主日实行禁食;从三时至七时半,远避群众,与主交通,虽确有不少搅扰引他改变习惯,但他为要与主交通,仍坚持不懈。”
辛氏有骄傲的难处。施旁恩伯说:
“……有时他深受骄傲所困,……他说到多次在事后深深自责,……好叫他更谦卑。他提到有一天在宫廷里没有受到该有的优待,因而向管家投诉,……他要求得着满意的看待,就立即得着了。但过了不久,他反覆思想这件事,发现自己的骄傲仍未除掉。他为此跪在主脚前流泪祈求,要得主的宽恕和恩典,并欣然放下了他的特权。辛氏说:『我答应主只清心跟随他,完全弃绝世界,不要尊贵,不受高举。从那时起,我那个决定一直没有改变,而基督的责备也常带给我喜乐。』”
1719年尾,他患重病,几乎要死,但他一心寻求主,只切慕快被主接去,绝没有想要求主延长的他的寿命。不过,主保留了他的性命,在教会的恢复中使用了他。辛氏写道:
没有想到会看到第二年的来临,……创造我的主又给了我无尽的恩赐,我都衷诚感领了。他救我脱离败坏的辖制,不然我会成为败坏的奴仆。我恨恶从前的懒散,以致过了许多虚妄的日子。我恳求主耶稣叫我有分于他的形像和样式。”
后来在离开巴黎的时候,他感到信徒的派别虽然不同,但大家都有共同的信仰。
受 聘
周游欧洲回来后,他受聘在德斯顿(Dresden)市作律师。每逢主日下午三时到七时,他把在德斯顿的家开放,用来聚会。施旁恩伯曾提到当时的情形:
“他坚持藉着神的恩,并倚靠基督,作为他盼望的根基,并且在言行上,勇敢地表明他,以致世人再不希冀引诱他改变立场。他诚心继续他最大的职志,就是传扬福音,并因与贫苦、朴实的神的众儿女来往,而感到满足。”
“他住在德斯顿的时候,他的家在主日一直有聚会,……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教导和亲切的谈论新约中的话语,然后一同祷告、唱诗。公爵回想那段日子说:『我们在主里喜乐,老幼都像小孩子般坐在一起。凡在我们中间显露学识的,我们都忍耐包容,等候以活的例证加以开导。』”
在德斯头,他以佚名出版一份刊物,名叫德斯顿苏格拉底(Dresden Socrate)。 第一次在1725年出版,目的在接触有组织的教会以外的基督徒。这份周刊第三次出版时就给政府充公了,直到公爵承认自己是刊物的作者时,才获准继续出版。辛氏在这份刊物上畅所欲言,施旁恩伯说他:“……立论惊人,辞锋厉害”。他想引导信徒真正经历基督,而脱离虚有其表。他责令信徒要作真基督徒,否则就不要再称为基督徒。
购买大庄园和结婚
1722年4月,他继承了祖业,就买下一个大庄园,包括伯佛尔斯杜夫(Berthelsdorf)的旧村庄, 目的在“培植主的美好园子”。他希望那园子成为一个避难所,收容各处不同身分、不同宗派受迫害的基督徒。
在买下庄园的同年,辛氏与雷斯女伯爵(Erdmuth Dorothea Von Reuss)结婚,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歌,描写基督对教会的爱。谈到他的婚姻,辛氏说:
“我绝不会以世俗的方式结婚;也不会选择与世同流的人作配偶。”
1722年9月7日,在他与女伯爵结婚前不久,他写信给祖母说:
“将来难免有困难,因为她嫁给我这个穷人,我想她只好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她要像我一样抛弃对地位和富裕的想望,因为那些并非属天的东西,只是人类虚荣的产品。她若想帮我,就必须投身于我人生的惟一目标,就是为基督赚得灵魂,并为此被人轻视和辱骂。”
他又写信给未来的岳母:
“我预料婚后会有许多困难,因为不管谁嫁了我,都只有贫穷。我亲爱的雷斯女伯爵不仅要与我同过舍己的生活,还得与我配搭,为着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去帮助人,为基督得着灵魂,并蒙羞受辱。……”
伯爵夫人是一个好帮手,也给辛氏适当的平衡:
“她在家中没有舒适或私人的生活。她常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十一时,忙着服事到她家来的弟兄姊妹。她私人的角落只有一张桌子和廉子,她很少到那里歇息,而且每次去都说抱歉。她不断工作、办事、写诗、聚会,在姊妹中间尽属灵的职事,……她和丈夫一样,从不花钱在小事或虚有其表的装饰上;但『为了帮助贫困者,或当神的旨意有需要时,她就大量捐输,往往超过她能力所及』;这一面她又和丈夫一样。”
约翰霍姆兹(John Holmes) 说,伯爵和夫人“同心同意,……决意奉献自己、儿女、时间和财宝给基督,并要服事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