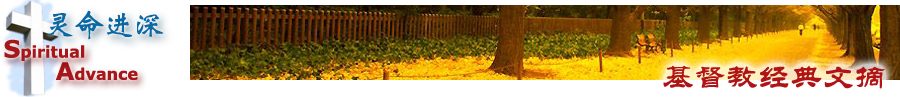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戰區宣教碩果累累(八)
瑪格麗.克賽特
15. 警报
从正阳关到日军前线有二十英里的平坦地区,正阳关的河流从地理位置上阻止了日军的入侵,我们到正阳关时,几乎每天都接到警报说日军要进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在二小时内出现在正阳关,城里的人经常被搞得心慌意乱,多数的房子已被炸毁,人们也没有心思去修,怕是修完还会被炸毁。商人们把货物都转移到城外藏起来,城里只留一小部分维持生意。有件事可以证明当时人们的惊慌程度:几个月来河水水位很低,船只无法航行,有一天,水涨了,有船来接梅葆和爱玛女士去霍邱主持圣经学习,当她们上船时,我看见城里的人都惊慌地跑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人说:“唉哟,日军开着摩托艇来我们镇上了。”街上一阵慌乱,妇女们急忙跑回家报警,见人就传这个消息。等了好久没见什么异常动静,她们才意识到是自己吓唬自己。开船的汽笛声和外国人的离开使她们乱了阵脚。
到了1941年的秋天,有一天我们在读报,隐隐觉得日美之间会发生什么大事,所以我给在寿县工作的琼斯女士写信,建议她来正阳关,以避免在日军管制区她的工作受阻,但是琼斯女士回信说,日军并没有干涉她的传教工作,万一发生不测,她会来正阳关避难。
1941年12月9日,温森特去拜访一个朋友,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这时一个中国人走进我家,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我说:“你怎么还呆在这儿?为什么不离开?”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一脸迷惑,“难道你不知道,昨天珍珠港被炸了!美方已正式宣布对日作战。琼斯女士在寿县被捕。日军随时有可能到这儿来,他们在这儿安排了特务监视你们,你们的处境很危险,而且你们还有两个孩子,这儿太不安全了。我建议你们撤离,撤到重庆。”
他继续说:“我姓刘,是个商人,进行日中双边贸易,我的生意很大,全国各地都有分店,我也是个基督徒,可以帮助你们这些传教士。”我担心因他商人的本性还能不能全心全意的服事主耶稣。但他的话让我提高了警惕。
刘先生刚走,我丈夫就回来了,他一进门,我就告诉他这消息,一向沉着冷静的温森特显得焦躁不安,“哎,让我们祷告吧,主会引领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
我家对面就是秘密警察局,珍珠港事件后,每次我这里有教会活动,对面的警察局就有人过来佯装参加活动,我劝他们离开,可他们咧咧嘴,装作没听见,他们还眼露凶光,死盯着女孩子看,搞得我们女子唱诗班的孩子很不自在;每次我和我丈夫出门,都有人盯梢。星期日教会活动时,温森特公开为琼斯女士祷告,几天后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塞给我一张纸条,之后匆匆离开,纸条是琼斯女士传出来的,她说她让送奶的狱卒悄悄传给我们消息,他已经从牢中一个日本军官口中得知我们在为她祷告。
每隔几天,日军飞机就来轰炸,我们很担心也许某一天日军飞机就会把炸弹投向我们。飞机一来,苏先生总会一瘸一拐地跑过来,眼中只有愤怒,口中却说不出半个字,我家没有防空洞,我就把厚被子盖在餐桌上,然后让苏先生和我的孩子躲到桌子下面,我和温森特则跑到外面观察情况。等日军飞机一飞走,苏先生就从桌子下面鑽出来,说声谢谢,然后一瘸一拐走回家。
这期间,有来自日战区的三名学生要去阜阳,他们带着中国基督教会一个朋友给我们的信,请我们收留他们,等他们接到批准去阜阳的命令再出发,那时温森特正在生病,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还得应付每天秘密员警的搜查,我每天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这三个学生刚在我家住几天,教会的一个主事对我说:今晚警察局准备动手,以特务的罪名逮捕这三个学生,因为他们来自战区。我说:“他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学生们有通关文书,我还亲眼见过呢,他们有证据,证明他们不是特务。”我连忙把这消息告诉这三名学生,建议他们立即动身去阜阳,可他们置之一笑,说:“我们不信传言,如果你担心自身安危,我们就搬出去住旅店。”他们真的搬走了。
第二天,旅店掌柜的儿子来告诉我:“昨天晚上三名学生被带走了,还被带上了脚镣,你们能救他们吗?”
“我们自己还是特务监视的对象呢,”我说:“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几天后,温森特病情有了好转,就去阜阳开会了,我和孩子在家。有人送来那三个学生传出的纸条请我们帮助解救他们,我一时没了主意,就在这时,警察局出来五六个大汉跑到我家搜查,他们要强行闯入我家的院子,我站在院门口,严厉喝斥,不让他们进,他们将我推向一旁和我争辩,但我依然不退让,最后,他们放弃了搜查的行动。那天晚上,我病倒了,得了一种叫“战争恐惧症”的病,温森特回来时,发现我得病很严重,赶紧请阜阳教会的护士来照顾我,我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几个月后,我才恢复健康,重新工作。
三名学生被释放了,逮捕他们的人也受到了惩罚,之后秘密警察局改成地方警察局,再没有秘密员警过来干涉我们的传教活动。
1942年圣诞节前几天的早晨,我丈夫在郊外主持敬拜活动,我和孩子们在家,当我给孩子穿衣服时,弗吉尼亚问我:“妈妈,那隆隆声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安排好孩子的早餐,我赶快到对面的警察局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局长显得很恐慌说,他也不知道,但已派人去侦察,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一整天镇上都能听到隆隆的声响,给教会做节日装饰的年轻人也在不停地议论:日本人真的来了该怎么办。
朱晨志(现在已住在正阳关)说:“我爸爸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一旦确定日本人来了,就逃到乡下,他现在每天吓得浑身哆嗦。”下午警察局长过来告诉我:就在我们不远处,中日双方交火了,但好消息是,日军不会进犯正阳关,你们不必担心。晚上,隆隆声消失了,这时温森特也回到家,他说:他一听说中日交战,就赶紧往回赶,生怕我再犯病。
我们过了一个祥和的圣诞节,但是刚过阳曆新年,我们被告知:这次日军真的要来了。我们说:“每週我们都收到这样的警告消息,还是再等等看吧。”那天晚上,好几个教会的主事都来说:局势严竣,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当我们犹豫不决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有官方消息,日军已从寿县出发,他们的数十辆卡车上都备有机关枪,极有可能在天亮前就到达我们这儿,不论各位愿不愿意,我们必须撤离,而且我建议我们中途不停顿,直奔重庆。”
我们一宿未眠,讨论该带些什么,最后决定: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箱子里只装少量东西,以备雇不到车,箱子太沉拿不动,另外我们将被褥打成卷带上。黎明时分,我们雇了一辆手推车,铺上被褥,裹好孩子出发,街上的人纷纷议论:“局势一定严重了,你看,连传教士都离开了。”知情的好心人告诉我们:“你们最好往北走,因为其他方向都有日军。”我们朝着霍邱的方向前进,一则想看看史蒂得夫妇现在的工作状况,二来要去接在分部工作的妹妹。天气非常寒冷,好在我们穿的比较厚,孩子们则蜷在被子里,但不大会儿,她们就嚷着要下地跑,我们三岁的女儿玛格丽特跑在头里,还兴奋地唱着歌:“当主耶稣到来时,我跑着去迎接祂。”
跟我们同方向撤离的还有正阳关的居民,我们还碰上从霍邱逃来的难民,我们问他们:“你们打算去哪儿?”他们说:“我们要逃离日本人,霍邱很危险,我们要到正阳关去。”儘管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听到他们的话,我们忍不住开怀大笑。
我们在妹妹的分部稍作停息,温森特一人前往霍邱去探望史蒂得夫妇。当他到霍邱时得知,离霍邱四十英里的岳西县已被日军攻佔,县政府和机关单位已经撤离,史蒂得夫妇已经准备好要撤离,我们约定在颖上会合。第二天清晨,我们步行了二十英里到达颖上基督教分部,我们刚要踏进教会的门,一位福音侍者,一副刚愎自用的神态朝我们喊:“你们不能进去,赶快走开,万一日本人来了,发现我收留你们,我全家就会跟着一起遭殃,快走!快走!别呆在这儿!”(不久这位侍者就被教会辞退了。)温森特态度强硬地对他说:这儿的一切都是教会的,他没有权利不让我们进。不一会儿,史蒂得夫妇带着两个又冷又饿的孩子也赶到了。我们一起在教会休息了一个下午,其间我们的先生们出去打听消息,消息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决定在颖上多待几天,看看还能不能返回我们各自的分部,但是那位福音侍者的态度让我们实在无法忍受,所以我们决定北上四十英里去阜阳。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连续走了两天多的路程,孩子们依然用被子裹起来坐在车上,半路上我妹妹好不容易雇了一头驴驮运行李,男人们赶着驴前进,我和史蒂得太太脚疼得厉害,走不动的时候就坐会儿车。
路上我们遇上一小股部队,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要开往前线,他们看上去个个精力充沛,步伐矫健,但是他们身上都没带枪。我们还遇上一些从黎皇方向逃来的难民,据悉几天前日军佔领了黎皇,这些逃难的人走得很快,不久我们就被甩在后面,看得出这些人基本上是政府官员或有钱人,但他们现在满脸疲惫,他们已经走了几天的路,其中还有小脚老太太,我们不由得心生怜悯。
那天晚上,我们找遍了街上的旅店,每个旅店都是满满的,没有空房间,住店的人几乎都是从黎皇逃过来的。最后我们到了城边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旅店,我心想也许这家店离城太远,才没住满人。可当我们推开房门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破桌子,一把断了腿的破椅子,一捆稻草堆放在牆角。露丝的两个孩子倒是异常兴奋,不停地叫着:“太好了,好美的地方啊!”我们把稻草铺在地上,拿出被子,哄孩子睡觉,然后我们进行祷告,求主保护我们这个夜晚平安,之后,我们和孩子一样进入梦乡。
当我们到达阜阳时,发现那儿的传教士也准备离开,但又有消息说局势好转,佔领黎皇的日军开到河南境内去了,其他部队都退回到原住地。几天后,我们重返正阳关的教会。
5月的一天,来自重庆总部的汤姆森先生来我分部视察工作。那天我们刚要入睡,就听到枪声,随即河边的战斗就打响了,我们猜想会不会是日军打来了,温森特连忙出去打探,一会儿他回来说:是士兵和刘先生的商船发生了冲突,商船要把一船的烟土和皮货送给日军,结果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第二天早晨,汤姆森对我们说:“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随时可以撤离,不用等总部的指示。”
16.最后一战
1944年4月,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虽然日军不段来骚扰,但我们的教会工作开展得颇有成效,这时美国领事馆下达命令,要求安徽、河南的美国公民向西撤离,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但教会总部也发出同样的命令。我们真的不想走,连续几天都争论到底撤离还是留守,还向中方打听消息,得到的消息都是:一切正常。这样一来,我们更是迷茫了,一天一个年轻人跑过来说:“日军正在筹划在这一带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我可不想把我的家人困在这座孤岛上,我得把他们转到安全的地方,我建议你们也赶紧走,再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一两天后,日军的飞机超低空在镇上飞行,扔传单,这时我们再次接到撤退的命令,第二天早上,我带着两个孩子乘船离开去往阜阳,而温森特准备留下观察局势的发展再做打算。
在阜阳我得知:一些传教士准备留下来,凡有孩子的妈妈都要和孩子一起撤离,单身女士也可以和这些妈妈们一起走,我们在二位男士的护送下,坐上一艘当地的船,船行驶几天后,我们到达河南边界,在那儿我们换乘一辆卡车,我们将行囊放在车顶上,又经过几天的车程,我们穿越河南平原地区到达洛阳。在这几天乘车时,为了防晒,我们每人在脸上涂上凡士林,但由于当时的卡车烧的是煤,我们的脸上挂满了一层厚厚的黑灰。
我们在洛阳城外等了一小时,时不时就看到日军的十架飞机在空中盘旋,这里的传教士几乎都撤走了,只有爱斯伯格先生、贝森先生和路德姐妹会的一个姐妹留守,虽然这时他们也在整理行装准备撤离,但还是热情接待我们一行人,安排我们住进教会的空房间。第二天早晨五点,只听汽笛长鸣,爱斯伯格先生大喊;“快点,快点!快进防空洞!”大家抱起孩子赶紧躲进防空洞。防空洞有40英呎深,楼梯又陡又窄,我们还没到达防空洞底儿,炸弹就爆了。我们在洛阳的两天,大部分时间都躲在防空洞里,一位勇敢的中国妇女帮我们做饭,然后趁轰炸间隙把饭菜放到洞口。不断有人加入到撤离的大军中,他们多数是河南的难民,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从窗子挤上一辆火车,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就连车顶、车厢链接处都没有空地。当时我真的怀疑,这么多的人,火车还能开走吗?我们一行中有人找到了座位,有的则坐在行李箱上,我们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只有晚上才开,白天就躲进山谷,一发现日军飞机,所有人立即跑下车,鑽进树林。住在附近的村民到火车前叫卖开水,麵包,我们就从窗口递出钱买些吃的喝的,不敢离开座位,生怕一起身座位就被别人佔了。就在我们的火车抵达西安车站时,车站被炸了,我从没见过人们跑得如此这般的快,瞬间火车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我们到了西安教会,走进一座斯堪的纳维亚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感觉像走进天堂。那天我们再次受到热情的接待,晚上盖着乾淨鬆软的被子进入梦乡。
我离开正阳关后,我丈夫也开始收拾行李,然后到霍邱取回史蒂得夫妇的行李,他把我俩家的行李装上船,沿河而上到阜阳,船夫很懒,不太卖力气加之风力大,他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阜阳。依照战争法则,他进城遇到困难。那时他很清楚日军已经沿河而上,离阜阳不到十英里。
他们一组传教士躲进山村里,打算万一阜阳打起来他们就躲在那里。一周后,他们发现日军没有进犯阜阳,又撤回他们的据点。这些传教士又都返回阜阳并且在那工作了一个夏天。当接到撤离消息时,科恩先生和爱玛女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平汉铁路到达红色中国。其他人依然留在原地继续传教工作。
之后,他们和美国的一支小分队取得了联繫,这支部队是在附近建军事基地的,部队答应带他们离开阜阳,所有河南、安徽的传教士都到郊外的一个村子集合,等美国飞机接他们回国,等候回国的人里还有一些美国空降兵,这些人在村里等了一个月,十七个人登上了飞机,可就在飞机要起飞的时候,飞行员让温森特站起来,说飞机上只有十六个降落伞,得有一人留下。温森特马上起身,走下飞机,挥手与其他人告别。
温森特又在教会分部停留了三个月,帮助教会处理遗留问题,最终他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一年零二天的分离后,我们在重庆团聚了。
17. 尾声—1946年的夏天
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安徽,一到蚌埠,我们遇到很多正阳关的基督徒,我们迫不及待地问:“教会工作怎么样?”
“很好,我们成立了许多新教会,发展了很多信徒,这些信徒已经开始了新生命。”他们继续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成立了阜阳—太寿联合教会,还有正阳关—霍邱联合教会,正阳关的教会工作有序进行着,五里铺(张士康住的地方)也建成他们自己的殿堂,那儿有一个年长的信徒负责日常敬拜活动,负责对信徒的深入教导,总之这里的每个教会工作井然有序,形势大好。”
我风趣地说:“看来我们没有回到这儿的必要了。”
“哪里的话,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指导,虽然我们现在能传福音,但是更需要你们讲解圣经,所有信徒更盼望聆听你们的教诲。”
那正是我们想做的事,因此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在那里教导圣经。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坐下来,加入到我们的祷告中吗?为安徽北部地区的教会祷告,为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硕果祷告,为我们的忠诚祷告。
(诗歌)祷 告
在远方有人在祷告 我不知道在哪里
在这有人在祷告 圣灵在运行
拯救世人心灵 脱离撒但掌控
有人在祷告 不知距离远近
不知他身份 有人在祷告
开启福音大门 赢得灵魂
身在远方的你啊 现在请为我们祷告
我的朋友祷告吧 直到撒但失去权势
祷告吧 请祷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