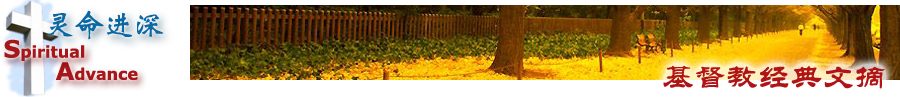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战区宣教硕果累累(六)
玛格丽.克赛特
我们一路开往正阳湾,因为日军已经向西进犯河南,日军东进的队伍离霍邱只有六十英里。到了正阳湾,我们看到,除日军司令部的房子比较完好外,其他房子已经倒塌,所有的教堂都夷为平地,信徒们也逃到他乡。我们在寿县下了船,借宿在一个朋友家,他们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在寿县我们得到消息说我们教会的考丝特恩夫妇也来和我们会和,他们要和我们同路去沿海的烟台看望上学的孩子。
几天后考丝特恩夫妇到达寿县,我们一起讨论要走哪条路才好穿越日军的佔领区。考丝特恩先生说最危险的路也许就是最安全的路。于是我们租了轿椅,女家眷坐上轿椅,考丝特恩和温森特走着,轿夫推着我们的行囊,踏上征程。很多逃难的人本想回到家乡但又不敢通过敌佔区,当他们看到我们要穿越敌佔区时也跟着走,很快我们的队伍绵延了一英里,队伍中男人扛着行囊,女人怀抱孩子,小孩紧紧跟在父母的身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美国国旗栓在一根竹竿上,考丝特恩举着国旗走在队伍的前头。
突然我们看到一个土匪站在路边,他手握武器,身着制服,满脸凶相,不断喝斥让我们快走,轿夫们也不知道是出于极度恐惧还是其他原因,开始奔跑,还不停朝我们喊叫,一下子我们被甩掉很远。不久又有三个土匪截住我们,挥舞刀枪盘问我们为什么要穿越日战区,我们的佣人镇定自若,对答如流,他们只好放行。第三次又遇卫兵盘问,他们还要扣留我们,但这次我们已经完全不害怕了。不久我们到达一个无匪区,看到一片岁稔年丰的庄稼,农民自由快乐地在地里干活儿,我们在一个大的集镇进行简短的休息,只见集市上人流如涌,人们无拘无束的置换自己的所需。好多人好奇地围着我们的轿椅,不停打量我们的孩子。我问他们:“在两国交战的时候,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太平?”他们笑着说:“是啊,日军是不远,那边也有游击队,但他们从没有交过火,我们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有时日军也来抢粮,游击队也不是很坏,我们用不着担心。”
不久我们到了一个小镇,那以前是个矿区,现在已经一片废墟,我们没有看到日军,很快我们到了镇中心的街道,考丝特恩先生询问日军的指挥部设在哪里,得到准确地址后,他带上几张名片去会见那里的日军长官,考丝特恩先生带的名片都是佔领浏安的一些友善日军将领送给他的。之后我们被安排到一家小旅馆过夜,日军长官命令我们明早六点一定离开,他身边的汉奸说:“他说的是东京时间六点。”
我们的确在六点出发了,我们乘坐一艘比较破旧的汽艇驶向蚌埠,乘船费用是日方提供的,由蚌埠我们转火车到上海,从上海我们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第二章 正阳关 1940年-1945年
十、返回正阳关
我们返回正阳关前,在上海停留了几天,等日军发给我们回安徽的通行证,然后我们乘火车到蚌埠,在那有停留了一个星期,其间,日军反覆搜查我们的行李箱,有一次他们粗暴地将行李箱拉开,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还说:“我们不查这些破东西,你们来错地方了,到其它地方接受检查。但明天别来,明天我们不办公。”我们赶紧将散落一地的东西装进被扯坏的行李箱里,离开检查站。之后的几天,日军不断盘问我们,终于有一天我们拿到了各种表格和通行证。
我们雇了十八辆人力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和物品,多数物品是给河南和安徽传教士们的传教材料。十八辆车在街上形成一道风景线,队伍庞大,因为日军沿淮河至寿县都有巡逻队,我们不能沿河走,只能绕道北上到太和县,然后沿沙河到正阳关。
第一天,风力很大,船上装的东西也多,行进速度很慢,我们沿淮河只走了六英里,天黑时分,我们到达河对岸,找到一个农舍过夜。我们走进那漆黑的屋里才发现这原来是个粮仓,我们三岁的女儿弗吉尼亚说:“妈妈,快点开灯!”不一会儿,有人送进来一盏煤油灯。当我们坐下吃饭时,一群农民围着粮仓,透过微弱的光往里看,还对我们不停地指指点点。
我们把堆在墙角的稻草铺在地上当作床垫,弗吉尼亚兴奋的说:“这样真的很像神的儿子耶稣。”清晨,我们被粮仓外的牛叫声吵醒,她坚信她有了和耶稣同样的经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心想:要是我们能顺利通过日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好了。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从对面走来,还不停的劝我们停下,但是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走了一段路,车夫说:“这下好了,我们摆脱了日本兵,不用担心他们再搜查了。”其实我们仍然在日战区,但是因我我们选择了绕开他们岗哨的路线,所以不会遇上日本兵。次日,我们终于到达自由中国地区,这时我们才松了口气。
我们住的地方很简陋,房间里没有傢俱,我们就睡在地上的床垫上,我敢断言,这个地方曾经是养猪用的,店主暂时把猪赶出去,让我们住,整个夜里,猪不停地拱门。房间又小又黑,有块墙皮都裂开了,冷风透过墙缝吹进房间,庆幸的是孩子们躺在婴儿车里,有厚厚的被子才没被冻着。
第八天的早晨,我们接近太和县,但我们还要渡过一个宽六英里的湖泊,当我们到达湖心时,突然刮起了大风,船夫全力在湖心抛锚停船,本来我们觉得两个小时就能渡过这湖泊,就把船装得满满的,船舱只有6平方英呎,高也就2英呎,我们只好挤进这狭小的空间,狂风刮了整整一宿,感谢主,我们还有这么个空间躲避风浪。第二天,天空晴朗,我们看到湖面上有好多被风刮翻的船只,我们再次感谢主保护了我们。
我们抵达太和县,留在太和工作的梅葆威廉姆森热情接待我们,他安排我们先进行沐浴,然后享用美味。
离开太和县,我们奔向正阳关,海伦欧文夫妇盛情接待我们,我们的交接工作完成后,他俩开始休假,这段时间,乔治史蒂得夫妇仍然在霍邱主持工作。
那时候的正阳关,距日战区寿县仅二十英里,寿县是淮河流域的一个小城,还是三条河流交汇的港口。
十一、正阳关教会
早在1887年,正阳关就有传教士传道,最年长的信徒还记得早期传教士的姓名及他们的趣闻。有些德国传教士就葬在这里的基督信徒公墓,最后在这儿工作的是伏格思牧师(Henry S. Ferguson)夫妇,后来伏格思师母去世,伏格思牧师仍然继续在这儿工作,到了1933年,伏格思牧师被抓,从此,他杳无音讯。【百度百科:伏格思牧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岁。】
安徽总是闹瘟疫发洪水,传教士们一直在这个地区发救济,这里的基督徒觉得每个传教士都很富有,他们只要讲讲自己悲惨的身世或处境,就能得到救济,教会也十分依赖这些传教士的供给,而不是主动去募集基金。他们有人还认为教会是外国人的,来教会参加活动就已经是给外国传教士脸面了。
土匪佔领正阳关时,教会解散了,但他们一离开,教会活动又恢复正常,这时,教会由三个人负责:苏牧师、老陈和王英美女士。王女士后来和我一起去霍邱开展工作。这三个人个性极强,经常有摩擦,在教会工作中总是闹矛盾,老陈有钱,传教士离开后,是老陈给教会很多的资助。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依然热情开展工作,发展信徒,每个星期日,教堂坐满人,苏牧师讲道;王女士开展妇女工作,并主持每周两次的妇女学习,可是多数信徒并不清楚他们自己的义务,认为来教会参加活动,捐几个钱就算尽职尽责了。
日军1938年佔领正阳关时,很多信徒逃到其他地方,不少人再也没回来过;苏牧师也逃离了此地,死在异乡;老陈虽也逃到外地,但不久就回到正阳关,1939年欧文夫妇到这里工作时,教会一派凄惨的景象,几乎没有敬拜活动,仅有的几次还是由以前看门人主持的。老陈,尽管他已经80多岁了,主持敬拜活动也颇吃力,但是他依然握有教会的大权,一切大事小情都要他点头批准。
当我们接替欧文夫妇工作后,觉得教会工作有了转机,每个星期日教堂坐满了人,还有很多妇女参加活动。我们每晚到南边郊外的街上宣教,传福音,在那里很多人获得了新生命。来这听我们讲道的人多数是新信徒,他们渴望瞭解更多圣经知识,虽然欧文夫妇教过读书识字,但还有很多人不会读书。教会工作有序进行,只是有几个顽固分子固执己见,他们坚持认为:自给自足、自筹资金只是年轻传教士的轻率决定,教会必须靠传教士出资维持开销。
老陈就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我们发现他在教会依然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当他说个“不”字,其他人就低声下气附和,我们一时无力改变现状。因为他不具有神灵思想,他的决定通常不会给教会带来益处,另外,他虽然对教会有掌控力,但对自己的儿子却无计可施,他的两个儿子都不信主。一天,有人告诉我老陈病了,我们去看望他,他有气无力地说自己要死了,然后陷入昏迷,但片刻他又醒了,这时他的儿媳妇问他:“你进入天堂了吗?你看见主了吗?”
“嗯。”老陈回答。
“主跟你说了什么?”她问。
“祂不理我。”老陈悲伤地回应。
几年前,老陈曾承诺捐给教会一笔钱,但是他一直没兑现承诺,现在他病了,于是叫来温森特,说要兑现以前的承诺,但是钱都在他儿子手上。之后老陈的儿子故意不让他接触温森特,几天后老陈带着内疚过世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承诺。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主持妇女学习活动,同时我发现来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少,那时,我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再有时间做大量家访,我就一周做一次家访,我主要访谈那些新信徒,给他们鼓励。一个周日妇女学习活动前,一位妇女偷偷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老会友不来参加学习吗?因为你不是每个周六都挨家去提醒他们,以前伏格思太太总是每周六挨家挨户提醒的。”
“他们入会多久了?”我问。
“三十年了吧。”她说。
那天下午,我对严肃地对妇女们说:“我听说有些老会友觉得自己受到了怠慢,因为我没有每周亲自去提醒他们参加活动,这些人在我出生时就是信徒了,可仍然指望我去提醒他们参加活动,我就是去访谈提醒,也绝不去这些老会友的家,而是新入会的、需要鼓励的新会友的家。这些会友应该感到耻辱,因为她们应该走出去邀请新的会友来参加活动,如果有人不知道星期日是哪天,好吧,我来告诉你!”会场一片寂静,然后我继续讲经传道。自那次以后,老会友按时参加教会敬拜活动,还不时引介新信徒。我也注意到,她们会为自己能发展新信徒而自豪。
十二、艰巨的任务
当时正阳关教会有两派,几个老会友坚决反对教会进行改革,还坚持强调他们这样做完全符合教会的章程,许多老信徒看不起年轻的信徒,说他们一知半解,不如他们对主的话理解得深入,以至后来很多年轻的信徒热衷讲主耶稣的故事而不讲解对主的话语的理解。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两股力量拧在一起,建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正阳关教会,以此荣耀主。一开始,我们举办圣经学习班,可老信徒说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已经很透彻,没有必要再学习,反倒是应该让年轻的信徒认真学习,好好理解主的话。鉴于我们没有时间开办特别学习班,我们就将所有会议时间都用到学习圣经上。在妇女学习班上,我用固定的时间带她们学习圣经,鼓励她们自学。这样的学习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我语重心长对她们说,正阳关靠近战争前线,我们会随时撤离,如果我们撤离了正阳关,她们必须要自己主持学习活动,才能保证教会的学习活动正常开展下去。起初,妇女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还说领会是传教士的职责,慢慢地有几位妇女主动学着领会,这样所有妇女也开始在家自学圣经,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她们还主动来找我寻求解答,渐渐地她们对学习圣经产生浓烈的兴趣,读圣经成为她们每天的功课。老信徒发现新信徒对圣经的理解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水准,有所触动,于是他们也认真学习圣经,以维护他们的声望。到了1944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离开正阳关时,妇女们已经完全独立主持活动了,而且每次活动都由不同的人主持。
教会中的年轻人看到妇女学习圣经热情高涨,也想组建一个圣经学习班,温森特就应他们的要求,组建了一个青年圣经学习班,并亲自每天授课,效果非常好。
我们迫切希望教会的每个成员瞭解并铭记教会的原则: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反覆强调教会是基督徒的教会,而不仅仅是传教士的,教会应该在神的引领下,由基督徒自己管理。当我们提出这个观点时,老信徒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以前的传教士从没有过这样的管理方式。但年轻的信徒非常感兴趣,迫切瞭解更多的理念。1943年,中国基督会主席汤姆森先生从总部到正阳关,他带来了办教会的新精神,内容和我们的理念其本相同,那些顽固的老会友觉得有些诧异,感到教会的理念有了巨大的变化,感到不适应,我们用了整整十天的时间讨论教会的宗旨,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同意采用我们的计划,教会终于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之后,新老信徒齐心合力,全心全意投入教会工作,很多人成为热心的事工,主动做以前他们不关心的事,每当他们发展新的信徒,都感到无比自豪。教会自给自足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信徒们纷纷慷慨解囊捐献,教会的领袖也意识到自己奉献的太少,感到羞愧。教会本想聘请全职的福音传道者,但是因为靠近前线的客观原因,没人敢应聘这个职位,值得称赞的是教会的妇女都成为专职的读圣经使者,她们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遣返了寿县的会长和美国人琼斯女士,寿县的教会的其他领导人就逃到正阳关,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在这儿继续指导寿县的传教工作,原本寿县的教会工作开展得就很有序,尽管日本人佔领着寿县,但是在这些领导人的指挥领导下,教会工作依然顺利进行。我发现这些人个个优秀,每天热情高涨地投入工作,同时,他们也给我们正阳关教会很大的帮助。更让我们欣慰的是:寿县教会在没有领袖和传教士的情况下,教会工作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各种活动井井有条,还成立了很多教会分部,所有教会都遵照我们办教会的宗旨(自给自足)开展工作。年底寿县教会征求我们的意见,问能不能在我们的地区举办年度聚会,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当召开年会时,我们教区很多基督徒参加了活动,他们感到很受教育。寿县基督徒们的见证,也帮助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者放下偏见,最终,所有信徒统一了思想,通过了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章程。
寿县教会的一个长老叫王颖梅(前面曾提到她),她由琼斯女士推荐就读教会学校,在学习期间,她写信给我请我原谅她在霍邱的行为,现在她已经抛弃了旧我,成为一个新我,她要用毕生的精力服事主。她还说,也许有一天主会允许她再次与我共同服事主。我深知,实际上,主已经把她当成一个恩赐送到我们面前,无论是在霍邱还是在正阳关。
正阳关的教堂非常小,让小孩子和大人们一起参加敬拜活动是个问题,我就在大人们进行敬拜活动的时候,举行儿童学习活动。开始来的人很少,慢慢地人越来越多,最后足有100人,到圣诞节和中国阳曆新年的时候,人数达到了300人。于是,我聘请教会年轻的信徒帮助负责儿童学习活动。教会还决定,把儿童按年龄分班学习,列入星期日活动日程,这项学习在敬拜活动之前进行,所以教会的很多信徒主动承担授课任务,于是我先对这些要授课的信徒进行培训,但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撤离正阳关的命令,周日的学习班活动没能成行,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这个学习班能开课。
我一边全职作教会工作还要操持家务,照顾两个孩子,因此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去对信徒进行家访。于是我和教会的几个负责人商量能否把我们的教区分成片,每人负责一片,她们都支持我的想法,我们进行讨论,拟定计划,划分各自负责的地区,然后进行祷告。当她们要离开时,胖刘姐拍着我的肩说:“别再为家访的事操心了,我们会干得很好。”实际上她们真的干得很出色:凡有不来参加活动的,她们就及时进行家访,有生病的,她们就为其祷告,她们还领新人参加活动并坚持到这些人家里作访谈,鼓励他们不要中断参加活动,在她们的努力下,新人都坚持参加敬拜活动。就这样,众人一起努力,硕果累累。(续)